
抗战老兵任铮
老兵简介:
姓名:任铮
出生日期:1919年5月27日
去世日期;2016年1月5日 (享年97岁)
籍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
居住以及逝世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第一小学家属院
抗战简讯:任铮于1939年考上黄埔军校第17期,1941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部电台台长、上尉军衔。1942年5月从野人山撤退回国。
引言:76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历史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国而战的英雄。
从1942年春天到1945年年初,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中国远征军沿着滇缅公路向缅甸境内挺进。这是我国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人首次踏出国门,赴海外作战。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甸战场,后被日军切断归国通道,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决定率部从野人山撤回云南,这片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瘴气弥漫、毒虫遍地、野兽肆虐,为了回到祖国,4万多远征军魂断野人山,成为世界军事史上最悲惨的战争之一。
任铮是曾经活着走出野人山而幸存的老兵。时隔七十多年,每每提及失去的战友,老人潸然泪下。

以下内容是笔者在2015年5月的采访:
阳光透过参天的白杨树,把树叶投影在明晃晃的柏油马路上,路边的操场上活跃着孩子们欢快的身影,耳边回荡着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穿过兵团绿树成荫的小路,走进第六师五家渠市第一小学深处的家属院,抗战老兵任铮的家就在这里。
“你们来的正好,再晚来一两个月,恐怕见不到我了……”今年96岁的任铮看到记者和志愿者一行上门拜访,面带微笑的招呼着。
“哪里,哪里,您至少要活到100岁!”关爱抗战老兵新疆志愿者团队负责人丁德保(2017年7月22日病逝)托着任老的手说。
任老不时的咳嗽、喘息,在儿子的搀扶下,努力从沙发上颤颤巍巍的站起来,他再次确认了当天的日期:2015年5月24日,他希望,至少要活到日本向中国投降70周年那天。
鬼子打到了家乡
任铮的老家在河南温县,出自书香门第,回忆抗战往事,任老心潮澎湃,眼神中闪现出“意气奋发少年郎”的模样。
1937年夏天,任铮从县城中学毕业后,来到开封,准备继续求学,但求学之路被战事打乱了,“那时候,天上是飞机,远处有烟雾,耳边还有枪炮声,大街上到处都是拿着行李逃难的人,有好多学生,有开封本地的、还有东北的、河北的、华北最多,他们往鄱阳湖那边跑,露宿在岸边。”任铮说,看到这种人心惶惶的紧张局势,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鬼子来了,无家可归啊!

任铮敬礼照
当时,开封的街头和学校到处贴着抗日救国的布告,在一则布告前,任铮看到,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通讯兵团训练大队招生,任铮毫不犹豫的去报名考试,考试科目里还有英语,因为当时通讯语言是由数字和英文组成的,任铮说,多亏自己曾学过英语,参加完考试,三四百人只录取了六十多人,任铮被分到了无线电专业班。
1937年底,任铮和同学们乘火车从郑州到武汉汉口的训练大队,为了尽快学以致用,学员们不分昼夜的学习密码、密语、发报。随着战火四处蔓延,学员们不断搬家,先后搬到过湖南长沙的中正路、湖南洞庭湖旁的南县。1938年夏天,学员们又转移到湖南东部的醴陵,训练大队的教官都是黄埔军校5、6期毕业的,任铮还记得当时的大队长叫沈蕴存,中队长姓陈,还有一个队长叫李荣。
学习了一年的无线电知识后,任铮于1938年毕业,这时候,训练大队已经搬到湖南的常德,任铮被分到设在湖南南县的“长沙防空司令部”的电台工作,从那时开始,无线电台成为任铮坚守的抗日阵地,“嘀嗒嘀嗒”的莫尔斯电码,是任铮最亲切而熟悉的声音。随着战事变化,任铮又辗转桂林、到重庆的“防空司令部”,这个司令部驻地在四川广安县城的图书馆里面,任铮记得,对面就是杨森公馆。
“那时候,电台的工作特别重要,比方说,我们接到日军飞机的飞行信号后,立即把电报准确的发到指挥部,指挥部根据信号攻打敌机,所有的命令下达,如何应对,让哪个部队出击,都要通过电台发出去,这关系着战争的胜败。”任铮说,当时,他所在司令部有三、四个报务员,深感责任重大,最担心的就是电报没有及时发出,贻误军情。
随着战事对通讯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1939年,任铮考上了黄埔军校第17期设在贵阳的通讯兵科独立第三大队,在这里,任铮又进一步学习了通讯知识,1941年,任铮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昆明行营通讯指挥部。

任铮接受采访
远征撤退 踏向“魔鬼之居”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了缅甸的首都仰光,切断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路——滇缅公路,威逼印度和中国的大西南。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任铮就是这10万名战士当中的一员。
那一年,任铮被派到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部任电台台长,上尉军衔。司令部在缅甸缅甸中部城镇眉苗(Maymyo)。
回想远征缅甸,任铮说,当时,远征军都是坐着大卡车从中国到缅甸的,车白天黑夜都在开,不记得开了多少天,只记得到了目的地,看到了大象。
在缅甸,任铮所在的电台主要负责和中国远征军第五军联系,当时,杜聿明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后来因为盟军配合不力,战斗失利,远征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不得不撤退。可残忍的日军欲置远征军于死地,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通道。远征军的将士们跟随杜聿明将军选择了一条无比凶险的回归之路——穿越一片叫做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回到国境。
对于这条可以回到祖国的撤退之路,任铮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虽然,他听到了很多“进野人山必死”的传言,但野人山到底有可怕,在没有进入之前,他毫无概念。

任铮与志愿者李萍
“记得,在缅甸的曼德勒(曼德勒是缅甸中部偏北的内陆城市),我们接到命令,把重型武器装配全部就地销毁,包括我们的电台,那些装备全部被浇上了汽油,火焰燃的老高。”任铮说,之所以这么做,据说,当时是为了减轻负重并阻断日军的追赶。
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撰文说到部队进入野人山之前的情况:“5月中旬,部队到达曼德勒以北500多公里一个村庄,就再也没公路了。军长下令把重型装备全部集中销毁,原来乘坐车辆的1500名重伤病员就地安置。”
目前身在安徽合肥的原第五军新22师卫生兵刘桂英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撤退野人山时说,“有军官把1500个伤兵集中起来问他们,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后来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 “看到那么多伤兵自焚而死,我们爬在地上哭起来。”刘桂英说,“是哭他们,也是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
邱仲岳将军在《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二)——一个老兵的亲身经历》中写道:“……(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黄昏时分,第五军军部与第六十五团(新二十二师所部)主力到达莫的林(Mode)宿营,军直属部队及各部队伤患一千五百余人进驻莫的林东南边的村子里……5月16日,第5军主力纵队徒步出发,伤病员及辎重全部留在莫的林,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一千五百余中华儿女,咸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鬼的志节,宁为烈士死,不做降俘生的决心,慨然于5月21日凌晨一时引火自焚,含恨而终!

任铮年轻时的照片
所谓“死路一条”的前路位于缅甸密支那以北胡康河谷一带的原始森林,位于中印缅交界处,方圆近300公里,遮天蔽日、野兽肆虐,瘴气弥漫,缅语意为“魔鬼之居”,因曾有野人出没,而又被当地人称为“野人山”。穿越这片原始森林前往中缅边境,直线距离为138公里。
“在进入野人山之前,我的一位要从印度撤退的好朋友李国栋告诉我,野人山特别凶险,他送给了我几盒火柴、两双胶底鞋、一件雨衣。我的一位同学送给了我治疗感染、发烧、恶性疟疾等疾病的药品,我把一支手枪送给了他。”任铮说,后来看来,就是这些珍贵的物品救了我命。
据抗战史专家戈叔亚考证: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约4万多人,在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率领下,途经野人山撤退。
就差一步 我的勤务兵没跟上来
“刚进山的时候,还有工兵在前面开路,我们跟在后面走,原始森林的树高的很,树叶又大又密,阳光都照不进来,白天跟晚上一样,潮湿、闷热的透不过气,我们几乎都穿着草鞋,没人戴手表,我手里有个指北针,我身后还带着四个通讯兵。”任铮回忆说。
据史料记载,1942年5月的野人山,闷热难熬。从未受过野外生存与丛林作战训练的远征军官兵,只能靠着几张并不准确的地图和少数指北针,摸索前进。
对于时年23岁的任铮来说,发现队伍慢慢溃散的时候,他已感到不安,“我们进山没几天,就开始下大雨,雨像石头一样砸在身上,我立即穿上了雨衣,雨太大了,雨衣都穿透了,不一会就在地上积成一片水洼地,有些地方开始爆发山洪。”任铮说,很快,工兵也没法开路了,起初,队伍齐整的在原始森林里穿行,后来,人越走越散。

任铮年轻时的照片
缅甸的雨季从每年5月中旬开始,至10月结束,这期间,野人山终日笼罩在倾盆大雨中,雷电闪过,“魔鬼之居”的魔鬼开始苏醒。
1942年5月13日,就在杜聿明向担任断后任务的第九十六师发出“自行突围”的命令后不久,一直跟随他前进的军部发报员不慎坠崖身亡,唯一的电台损毁。进入野人山的远征军官兵,从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眼看,进山时带的粮食越来越少,一股不安的情绪开始在官兵中蔓延,随着热带丛林的雨季到来,山间的小涧也变成了汹涌的河流,整个队伍在没完没了的暴雨中慢慢溃散。“在行走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会丧命。”任铮回忆说,一路下来,他看到身边的好多战友滑进河里就没起来。
死亡正一步步逼近行进中的中国远征军。
任铮回忆说,身为电台台长,原本,他身边还带着四个通讯兵,但走着走着,有病死的,有滑进沼泽地的、有被山洪淹死的,最后只剩下一个兵,他们只能一路朝着北走,往祖国的方向前进。“他是我的勤务兵,我的毕业证、黄埔军校的通讯录、电码本都在他那,他帮我背着行李,四川人,特别能干,人也特别好,就差一步,就差一步他就跟上我了……” 说到这时,任铮突然忍不住哽咽,眼泪夺眶而出,那是多年来,任铮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幕。

已故新疆志愿者团队负责人丁德保为任铮佩戴深圳龙越基金会发来的纪念章
当时,他们在大雨中过一个窄窄的木桥,任铮刚刚过了桥,正等着他的勤务兵过桥时,这时,工兵团赶来拆桥,以阻断日军的追击,任铮恳求工兵团等等,等他的勤务兵过来再拆,但军令如山,他们必须在3分钟之内拆桥,分分钟时间,木桥解体,随着翻滚的激流迅速消失……
眼睁睁的看着桥没了,在悲伤和恍惚中,任铮远远的泪别他的勤务兵,心如刀割,他背着行李,无助的站在那里,向任铮挥手道别,“没吃、没喝、又没药,他过不来就是死啊!”任铮泣不成声。
事实上,在最后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官兵之中,任铮经过多方查找,也没有找到他的勤务兵。
一觉醒来 发现他们都死了
泪别了他的勤务兵,任铮悲伤难平,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行,渴了喝雨水,饿了吃些野果野草,但那些东西很难消化,又饿又累,疲惫不堪。
任铮不知道,更大困难还在后面,野人山由于不见天日、阴霾潮湿、腐烂气息令人窒息、漫山遍野的蜈蚣、蚂蝗、蛇、以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毒虫到处肆虐着、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方圆数百里都是无人区。

任铮与已故新疆志愿者团队负责人丁德保
最厉害的是蚂蟥,“那个蚂蝗比中国的蚂蝗大好多,大拇指那么大,吸了血,有手掌那么长,手腕那么粗,它咬到你,你根本不知道。” 任铮说着拍了拍了自己的右腿,行军休息途中,任铮发现自己的腿上鼓起来好几个大包,每个包都露出一节蚂蝗尾巴,才知道是蚂蝗钻进去了,任铮拼命拽,只拽断了一小节,这时,沿路行军的战士告诉他,蚂蝗钻进肉里是拔不出来的,要用力拍蚂蝗叮咬的部分以及外露的身体,这一拍,拍出来七、八条,全都吸饱了血出来了,每条都有两根食指那么粗,任铮说,至今为止,他腿上被蚂蝗钻过的地方都没反应。
热带雨林的虫子是能吃人的,任铮看到,沿路有很多走不动的官兵,躺在泥水里,瞬间就被蚂蝗和毒虫包围,一路上,任铮看到了太多将士们的尸体,还看到有病倒的将士自杀的,也许,这对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他们来说,甚至是种解脱。
“在野人山那种环境下,心理承受能力确实是到了极限了。”任铮说,沿路看到太多尸体,那种惨状没法形容,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山里走了多少天,只是一路朝着北走,走着走着,任铮在一片山谷里看到了房屋,原来,那里是中国的华侨,他们在深山里采玉,他们力劝任铮留下来和他们一起采玉,因为再往里走,就是死路一条,“我是一名军人,我必须遵从军令回到祖国。”任铮说,当时,就是这个强烈的信念在支配着他,临行前,华侨送给任铮一些干粮、铁锅、火柴、以及一块像成年鸽子一般大小的红玉,那块红玉以备不时之需。

任铮佩戴纪念章照
依然不知道在深山里走了多久,当最后一点粮食吃完后,任铮只能吃野草充饥,任铮说,之后啥也吃不下,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不得不扔掉了那块在当时看来,价值连城的红玉,走着走着,任铮开始发烧、上吐下泻、拉出来的都是黑水,他知道,自己得了恶性疟疾,行军途中,很多战士都是得了这种病死的。
“不到迫不得已,我是舍不得吃那几片救命药的,那时候,我真的感觉自己快死了,眼前就是一片白雾,任铮用树叶舀了一点雨水,吃下药片,极度疲惫之下,任铮看到一个用芭蕉叶搭建的小木棚子,在雨林里,找一块能遮挡雨水的地方很不容易,任铮使出浑身力气爬上棚子,此时,看到上面已经躺了三、四个战士,看起来都在睡觉,极度疲惫的任铮倒下就睡。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我看他们都没动,不对啊,好多大虫子在往他们身上爬,再看脸,青灰色,还有黑斑,原来,他们已经死了……”任铮说,人命还不如一根草,那一刻,他并不感到恐惧,沿途看到太多战士们的尸体,有些被蚂蝗吸血、蚂蚁啃噬、大雨侵蚀后,数小时后就变化了白骨,此刻,对于任铮来说,最大的恐惧是,怎么活下去?

志愿者为任铮送来龙越邮寄来的挂历
脚趾头插进石头缝 翻越高山迈向国境
暴雨、饥饿、沼泽、毒虫、死亡、深陷野人山的任铮感到前路绝望。
杜聿明曾在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写到野人山撤退:“……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以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
野人山的生水是不能喝的,喝了就会死,但对于极度饥饿、且没有原始丛林生存经验的中国远征军来说,饥不择食,很多战士在喝了野人山的生水后腹泻、呕吐,直到倒下,再没有爬起来。
“一路走来,尸体遍地,每具尸体上都是成群结队、大多出奇的虫子。”任铮说,有一天,终于不下雨了,很难得的看到了太阳,他走到一个河谷边,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不知不觉睡了过去,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腿泡在水里,整个左腿泡涨了,肿了好大一圈,“太累了,睡着的时候,腿荡到了水里都不知道。”任铮说,至今为止,他的左腿常常感到麻木。
在艰难的跋涉中,同乡送他的胶底鞋全都走的破烂不堪,直到走没了,最后,任铮只能光脚前行,顺着指北针,任铮开始翻越一座高山,“那山很陡,我把脚趾头插到石头缝里,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退路就是死,我只能前进。”任铮说,越往上爬越冷,他后来才知道,翻越的那个山叫——高黎贡山,他的脚已经迈到了国境。

任老去世信息截屏
高黎贡山位于云南西部怒江大峡谷,坐落于怒江西岸,是横断山脉中最西部的山脉,北连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500米,是中缅边境上的一道天然屏障,然而,高黎贡山的山顶常年积雪,由于中国远征军还是夏季装备,缺乏御寒的冬衣,成百上千的远征军千辛万苦的穿越了野人山之后,却在寒冷的高黎贡山被活活冻死。
“我用最后的力气爬到山顶的时候,看到了白雪,可我身上,只挂着几缕破布,冻得要命,我不能停,停下来就会冻死。”任铮说,寒夜里,他光着脚在雪地里不知走了多久,突然看到了火光,是从一个洞穴里发出来的光,走进一看,有四、五个战士围坐在一起烤火取暖,他们看到任铮,那种无法言说的表情令任铮终身难忘,和战友们挤在一起烤火的时候,任铮忍不住哭了,绝处逢生啊!
后来,残兵们结伴回到了云南,然而,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官兵们并不感到欣喜,那些逝去的将士是他们的朋友、同乡,是曾经生死与同的亲密战友。
1942年8月底,随着第九十六师最后一批残兵翻越高黎贡山,抵达云南剑川,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至此结束。根据杜聿明将军的粗略计算,中国远征军10万人,生还者仅有4万,战牺牲有1万多人,也就是说,有4万将士是在撤退途中非战斗牺牲的,他们的尸骨至今还在野人山的丛山峻岭之中。
“同路的好朋友,好同学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回来,我难受啊!”任铮说,在云南的兵站,当他把那身穿了几个月、已变成几缕破布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全身都是脓疮和密密麻麻的虱子,在当地治疗的很久,任铮身上的脓疮才勉强愈合。
翻越野人山对任铮来说,更难治愈的是心理创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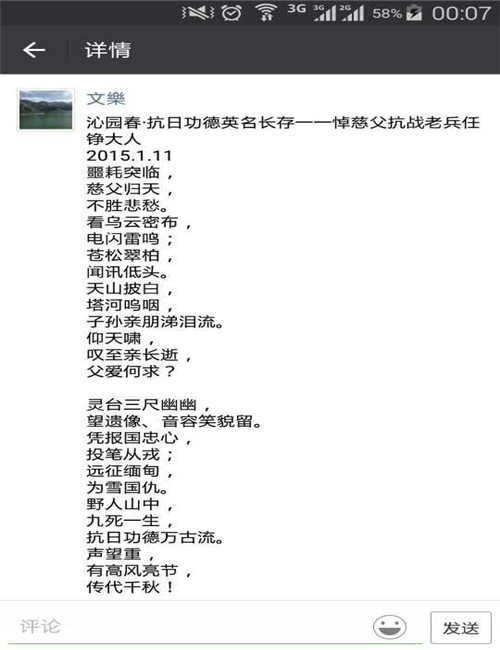
任老去世信息截屏
野人山大撤退,导致中国远征军走向惨重的毁灭之路,全程穿越野人山的将士死亡率接近90%,杜聿明本人也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身体逐渐康复后,任铮被调到“交通部公路总局无线电总台”第二台工作,脱离军队。先当报务员,后当台长,同时兼任《大公报》电务员,负责收集日本,美国的电讯。
抗战胜利后,任铮回到重庆通讯兵三团,1949年在重庆起义。后来,任铮在解放军西南通讯兵学校当教员,1952年转业回河南老家种地,教书,之后在当地成立了“童声豫剧团”。195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河南招收豫剧团员,任铮和他的豫剧团,全团81人被招录到了新疆,定居新疆后,改名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童声豫剧团”,任铮担任编剧,他编剧的剧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艺术宗旨,在整理和改变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创作现代戏等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连文革期间还在演出他编的剧本,豫剧团后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豫剧团”,任铮一直在豫剧团工作,直到退休。
如今,晚年的任铮住在儿子家,他极少向人提起那段抗战经历,哪怕是儿子。
“这些年,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到野人山了,我的勤务兵,多好的小伙子,我是踩着他们的命活出来的……”七十多年来,这一幕在任铮的脑海里反复上演,战争的残酷记忆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而这丝毫不会因为岁月的增长而消退,反而日久弥新。
采访临近结束时,任铮为我们唱起了《黄埔军校军歌》,用手拍打着膝盖,声音铿锵有力: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注:老照片为翻拍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