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李岚、陈何毅
整理者:陈何毅
采访时间:2013年4月
采访地点:浙江省永康市徐新容家中
讲述者简介:徐新容,曾用名徐逸容,1918年出生,浙江永康人。1937年始,先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第十七期通信兵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远征军通信兵第6团第2营任少尉报务员,入缅参战后升任中尉班长。滇西反攻开始后,调到云南楚雄的兵站总监部任职少校科员。抗战胜利后,任通信兵独立第3营上尉副连长。1947年,调到陆军通信兵学校军官训练班第二队,任区队长兼教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回到家乡永康。
采访手记:徐新容很和善,身体好,记忆力也好,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聊了3个多小时,部队的番号,长官、战友的姓名都记得很清楚,经历的事情也能细致地讲述。也许这段经历实在太刻骨铭心,太难以忘怀,每个老兵一说起都会滔滔不绝,徐新容老人也不例外。随着他的叙述,这些“陈年旧事”依稀展现在我们眼前,令我们几有身临其境之感。他还给我们演示了电报台的工作情形,虽时隔多年,操作仍然极为熟练。
当老人说到惠通桥被炸时,自己过了桥但部下没能过来,后来得知没能过桥的1000多名中国军民都被日军乱枪扫射而死的时候,老人哽咽了……几十年来深藏心底的那份无奈和内疚从未消退,也许这份无奈和内疚将会伴随老人走完余生,也许在某天某个地方听到昔日部下安好的消息才能让老人释怀。
考入有无线电教导大队
1937年7月,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南京考学校,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初试录取了我。日军的飞机轰炸南京后,学校包了条船把初试录取的学生送到武汉。到了武昌,住在营房里等着复试。我闲着没事干就去逛街,碰到一个同乡李宝庠。他是黄埔军校第八期的学生,代表通信兵团学校来招生。
当时全国只有一个通信兵团,通信兵比较稀缺。他跟我说通信兵团学校的老师是德国人,机器也是德国的。必修课有内燃机、电机工程、电池学、有线电、无线电等,学制3年,资格跟黄埔军校一样。我本来就喜欢数理化,所以听了很心动,就去考了。一连考了3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都考上了。直接被送到湖南醴陵的通信兵有无线电教导大队学校学习。这个学校原来在南京镇江,后来搬到湖南醴陵,后来又搬到常德。
到学校头6个月是入伍训练,然后参加考试,我考到无线电队。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敲打发报机,我们在座位上就可以收,同学之间也可以互相收发电报。练习的时候是收发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一般是以收为主,要求每分钟收140个单字以上。数字1代码是“嘀嗒”,2是“嘀嘀嗒”,A是“嘀嗒”,B是“嗒嘀嘀嘀”。电视剧里的发报不是真的发报,真正的发报我们一听就能听出来。
毕业后,配属到第32集团军
随着日军占领的地方多了,部队的有线电和无线电报务员紧缺。我们就全天赶课程,把学习时间压缩。本来是3年的课程,一年半就算毕业了。1938年冬,就把我们派到部队上去了。
我们这批同学一共有五六百人,被分派到全国各地。我被派到安徽第32集团军通讯兵团第1营第4排第3班,刚开始当准尉见习,3个月以后就升了少尉。第32集团军的长官司令是上官云相。一个电台规定是4名报务员加上1名台长,一共5个人。我的台长是教练所第一期的上尉,老资格,所以经常不上班;有教练所第五期的中尉报务员李振澍;有教导大队第三期的河南人杨琳中尉;还有教导大队第
八期的浙江人石简行。
我们通信兵团是通信部队,区别于部队通信。军、师里的通信营属于部队通信,我们是属于通信部队,整个部队都是搞通信的。当时有规定,我们通信部队只为军团以上的单位工作。我们的粮食、工资、人员都归通信部队管理,跟军团没关系。所以,我们只是配属在第32集团军工作。
考入军校第十七期,从江西徒步到贵州
1939年准备反攻南京时,就把我们总部从安徽徽州调往江西广德。当时为了打南昌,有十几个师驻扎在江西。我们的电台工作非常繁忙,整晚整晚的工作。电动的机器用坏了,就用手摇发电。我后来又被调到上饶第三战区长官部,驻地在周家墩。
这个时候,上面来了通知,说我们这些人学习时间不够,需要带薪补训,这次补训将会被归入中央军校第十八期,我当时就觉得吃亏了。此时,碰巧在贵州麻江的通信兵学校附设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来上饶招生,于是我就去报考。考上后,我从江西上饶徒步行军40多天到了贵州麻江。到学校后,身上都长虱子了。在这里,我进了通信兵科,学习有线电、无线电、有线电报、手旗通信等科目。别人都是考一次,读一次军校,我是考两次,读两次军校。
随通信兵第6团入缅作战
1941年冬,我们学校派包括我在内的15个同学,到中央驻云南的通信兵第6团。我在第3营第12连第4班当少尉报务员,负责驻滇参谋团的通信工作。
当时,我们是按照德国的“四四制”,一个营4个连,一个连有4个排,一个排有4个班,一个无线电班就是1个电台。所以,我们一个连就有16个电台。一个电台有4名报务员、1名班长,还有十五六名士兵。报务员只负责收发电报,其他的什么都不管。士兵负责登记、保卫、派送的工作。比如上级下命令要与某个师团的某个电台收发电报,那我们就进行收发工作。收发前后,士兵要负责登记,什么时间收到,什么时候发出去。电报收下来后还要送到译电室。无线电是保密的单位,怕有人破坏。士兵除了送电报的工作外,还要负责保护电台的安全。我们当时用的是德国人电动的机器,打仗的时候没有电就只能自己发电。发电、电池和充电机的管理都是由士兵完成,所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
因火灾被关禁闭
通信部队进入缅甸的时候,我刚从报务员升上去当中尉班长。我们坐车从云南昆明出发,经过畹町到达缅甸腊戍,住进英缅人的营房。住在这里的英缅部队是雇佣兵,他们把孩子、老婆和父母都带在身边。所以虽然只有20多个兵,但有四五十人住在军营。那些营房也不会太高,高的房子的房顶都是铁皮的。因为那里的气候不好,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冰雹。我们营房的房顶都是用茅草盖起来的,我是住第一个房子,第五个房子是负责有线电话的。住进营房后,我就马上开始通信工作,负责昆明行营、龙云指挥部、重庆统帅部与下面军、师的通信联络工作。通信工作一般从中午开始,到下午3点钟左右。
有一天,我正在收发电报。突然听到士兵说:“着火啦!”跑出去一看,房顶的茅草被做饭的火星飞上去点着了,本来想用水去灭火,但是几个印度籍浪人拿了几根棍子到处捅,这样一捅加上风势,火就更大。我看情况不妙,马上指挥士兵把电报机等机器从营房里抢救出来,20多间营房都被烧了。我去查看了一下,放粮食、被褥的房子给烧了,幸好放汽油和弹药的房子没有被烧。为了这件事,
我跟我们通信连的连长、排长,还有个副营长,都被抓起来关到第5军的卡车上。一关就是五六天,当时心里还觉得挺委屈的。
没日没夜地工作
在同古会战的十多天里,日军飞机每天都来轰炸。我们白天跑到山上躲警报,晚上信号比较好了,才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天亮。我们班上几个报务员的技术都不太好,所以半数以上的工作都是由我自己完成。我们的机器有大有小,包括收发报机。我就睡在机器旁边,半梦半醒地听着报务员的发报。一发现他们没打好的,就自己上。这样的工作状态持续了40天。
第200师从同古撤出来以后,指挥部集结部队在曼德勒与敌决战。通信兵第6团在缅甸有好几个电台,我这个电台被点名留在参谋团,其他的都下放了。有的到第5军,有的到长官部,有的到曼德勒。与昆明、重庆以及下放军、师的电报联络工作,都归我这个电台负责。由于只剩下我一个电台了,所以电报就更多了。每天都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当时我还是年轻,身体还能扛得住。
当时,日本人的共同社每天都会发布新闻。我安排少尉报务员毛步崧每天抄录新闻,上午一个钟头,下午一个钟头。这个人后来到美国留学去了,我一直以为他死了,到了四五十年后才知道他没有死。
我们的每个电报都有记号,看到记号就知道是什么级别。比如:十万火急——3676(急),看到这个记号就要特别注意了,是加急文件,一定要赶紧发出去。每份电报都要电报员所谓的签名盖章,每个报务员都会有一个签名代号。比如“QSL”代表一个签名,用我们的专业术语,“哒哒嘀哒嘀嘀嘀,嘀哒嘀嘀”,表示我给这份电报签名盖章了。每份电报都必须相当严谨,不能错发漏发。发错一个字都不行,那可是要杀头的。
撤退时,亲见日本的毒气弹
由于英军的配合不力,我军节节败退。有一天下午3点多,参谋团的沈定参谋来电话说:“小徐,现在战备行动,你们马上收拾好东西,到参谋团住所的停车场上车。”战备行动就是平时已经有一套紧急预案,在紧急时刻每个人就负责收拾一样东西,拿起来就可以走。他还很急地跟我说;“现在情况不妙,你不来,我就不管你了。”我一听他这样说,马上收拾好东西赶到停车场上车。就这样我们从腊戍,经过畹町、遮放、芒市、龙陵一路撤退回来。在龙陵住在一个教堂里,电台就设在教堂里面。
当天上午,日军的飞机来轰炸,我们拿起重要的东西就往山上躲。在山上看到飞机扔下蓝色长筒形的炸弹,跟平时黑色的炸弹不一样,而且下来的时候也没有爆炸。当时有些人是有防毒面具的,我们是没有的,老百姓也是没有。他们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叫他们把手帕之类的东西拿出来,沾点泥巴水或者沾点自己的尿,捂在自己的鼻子和嘴巴上,还要不能迎着风走。下山回城的路上,看到逃难回来的华侨吸进了毒气,死状非常恐怖。后来才知道,那个是霍乱菌的毒气弹。
我们回到教堂继续工作,没有接到命令是不能走的。当时的电报很多,参谋团因为没有架电话线,所以没有电话。中午12点左右,参谋团写了一张条子,内容是命令我中午1点钟撤离,让译电员交给我的卡车司机。他拿到条子后没有马上交给我,听说是被邻居的大妈拉住了,说自己在昆明有个亲戚,要他把女儿带到亲戚家,路上要是两人都同意的话就结婚。结果,等条子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当时已经听到枪炮声,我安慰部下说:“不要慌,打仗总会有枪炮声的,收拾好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了。”收拾好后,我们上车往城外走,一路上都是逃难者掉落的行李。我们一路开,一路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北门。出城没多久,龙陵车站就烧起来了。由于车站那有个油库,所以火烧得特别厉害,火光冲天。
目睹惠通桥被炸
行进中,我们车子的前轮坏了。幸亏车上有备用轮胎和工具,我们大家合力就把轮胎换了。然后就继续往前走。龙陵和惠通桥之间,也就六七十公里。但我们从下午出发,到第二天快天亮了才到惠通桥桥头。惠通桥是怒江上的一座吊桥,铁索吊着两边山头。当时桥上有宪兵守着,但还可以通行。快到惠通桥的时候有几个很陡的坡,很多车子都过不去,停在了路中间,搞得后边的车子都走不了。大家都觉得这样等不是办法。路上有不少部队的车,车上的兵都是有枪的。很多士兵拿起武器,临时组织起一个“护车队”,保护道路畅通。路上的车大部分都是华侨的,“护车队”指挥哪个车靠左哪个靠右。要是停在路中间又不能动的车,就直接推下山。我是通信班的头头,也带头参加临时“护车队”,有一辆车是我推下山的。
离惠通桥两三公里的地方,又开始堵车了。我奉通信指挥官尚公正(浙江缙云人)口谕,和几个体格好的兵一起到桥头看看情况。一路走到惠通桥桥头,估计桥两岸的车辆不会少于2000辆。里面有军车,但大部分都是逃难的私家车。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辆车一个人,起码有2000多人堵在那里。我们过桥后,准备找参谋团的团长、副官解决我们的问题。我看到交通部部长俞飞鹏在那,听说参谋团的团长林蔚、参谋长萧毅肃、工兵指挥官马崇六都在,但是我没有找到。准备往回走,宪兵不让我们回去,说上级有命令,惠通桥只准进不准出。我们就只好坐在旁边等,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个时候,有几个上身穿西装,下身穿军服,看起来不三不四的人硬是要过桥。原来他们是在龙陵做鸦片烟生意的,身上还带着枪。宪兵不让他们过桥,为弹压他们,就拔枪向天空放了两枪。这下就糟糕了,对岸乔装成华侨混在人群里的鬼子便衣队,听到枪声以为暴露了。把小钢炮、轻机枪从伪装卡车里面拉下来,向我们这边开火。他们只打公路,想着破坏公路后,我们就撤退不了了。日本的便衣队有20人左右,准备要冲过桥来。这个时候,听到有人喊:“炸了!炸了!”惠通桥“砰”的一声,就被炸了,日本的便衣队就过不来了。当时混乱得很,炸药应该是预先埋好的,马崇六是负责炸桥工兵指挥官。但是怎么炸的,我就没看见了。
保护密码本有功,奖励800法币
第二天,我到了保山收容所。我的机器、物品都没有了,连自己的衣物鞋袜都没了。幸好我的密码本还在,密码本对于一个电报员来说就等于士兵的枪。人在本子在,绝对不能丢。在收容所等了两天,都没有等到我的部下。只听到一个消息,日本人在惠通桥桥头抓了1000多人,让他们都跪在地上用机枪扫射,1000多人都死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心里很难受。
没过几天,听到日本人过来的消息,大家都很慌张地往外走。结果第二天,发现情报是假的,有个车子就把我们接回了保山。在路上看到满地都是尸体,那些尸体都是中了日本人的霍乱毒气弹,全身发紫,手脚发肿,把衣服都撑破了。60公里的路上本来有很多流动食品小摊,那时都没有了。后来,我们回到保山又住了10多天。上面有批钱发下来,说是奖励林蔚和萧毅肃炸掉惠通桥的奖金,发到我这是800法币。
我所了解到的赴印远征军情况
关于赴印的中国远征军,我听说了一些情况。他们是从云南坐飞机到印度,上飞机的时候穿得是棉衣,下飞机时天气很热,把衣服一脱往旁边一扔,就汽油一洒全部烧掉。后来觉得把衣服烧掉很浪费,就把衣服脱掉了光着膀子上飞机。结果飞机经过“驼峰航线”的时候很冷,很多人都冻病了,有的还冻晕了。美国人就以为我们把身体不好、生病的兵送去,所以派医生在云南上飞机之前给士兵体检,合格的就在手腕上盖章后就可以上飞机。
当时是“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有的身体不太好的,就自己找个芋头挑个章盖在手腕上就可以过关了。飞机场的警卫连连长是浙江缙云人章公武,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的,参加过淞沪抗战,跟我是永康中学同学。那个时候驻印军是没有人贪污的,人员都是满编,只会多不会少。
滇西反攻中的电台战
我回到昆明通信兵第6团报到后,继续负责电台工作,具体点就是,我在西南行营龙云指挥部通信兵第6团第12连第4班。我们一个连16个电台,也就是16个班。第1、第2班的班长可当上尉,第3、第4班的班长最高可以当中尉,第5、第6、第9、第10、第13、第14班的班长都可以当上尉,所以我还是中尉班长。当时德国人的机器有5W、15W、50W三种,在缅甸用的是15W的机器,回到昆明后就用上了50W的德国机器。工作了一年后,由于我的工作表现不错,就把我调到大理的第11集团军宋希濂的部队,取代原来的班长,他是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的,电台工作搞得不好。
1943年反攻时,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搬到云南楚雄,我被调到楚雄兵站总监部当少校科员,兵站司令是司可庄。宋美龄访美后,司令长官部从楚雄推进到保山。我们两个集团军开始反攻滕冲、松山。在攻打阵地的时候,通信兵是不用去的。但是攻下来以后,我们有时候就要去。由于我们是负责管理器材补充、使用的工作,所以不用去阵地。这时,我们已经改用美式器材了。
我们的部队渡过怒江后,攻打腾冲十多天都没攻下来。卫立煌觉得奇怪,为什么日本人好像知道我们要怎样打似的。于是,紧急召集指挥官开会,才发现原来有一男一女两个报务员坐美军飞机去游击区的时候,错误降落在日军机场,被日军抓住杀害了,报务员的密码本落在日军手里。日本人在芒市、遮放的司令部设置了一个专门收集电台信号的电台,检测我们电台的信号,利用那个密码本破译我们的电报。卫立煌知道后,没有请示上峰,就直接命令部队先放弃腾冲,调过来从龙陵攻打松山。
抗战胜利后,各奔前程
1945年,盟军收复仰光后,新编第1军就被调回国,我亦回到通信兵独立第3营,当上尉副连长。随着中国远征军大捷,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为历史,直属各单位科室人员各奔前程。1946年夏,我随部队辗转上海、济南、南京等。1947年,调到陆军通信兵学校军官训练班第二队,当区队长兼教官。
当时想调去学校不容易,一般都是毕业后留校。因为这个学校的教育长是曾教我代数、几何的教官,湖南人李昌来。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湖南大学毕业,公费去英国留学,抗战时期一直在美国工作。抗战胜利后,回来当这个学校的教育长。他就把我们这几个当年学习成绩比较好的,调到学校来当教官。当时我想考陆军大学,考陆大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是要在前方打仗带过兵;二是坐过办公室;三是在军事学校带过学生。毕业后,一般都是师里的参谋长,好点的都是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回永康休假探亲。其间,学校打电话通知我去台湾。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留在永康。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2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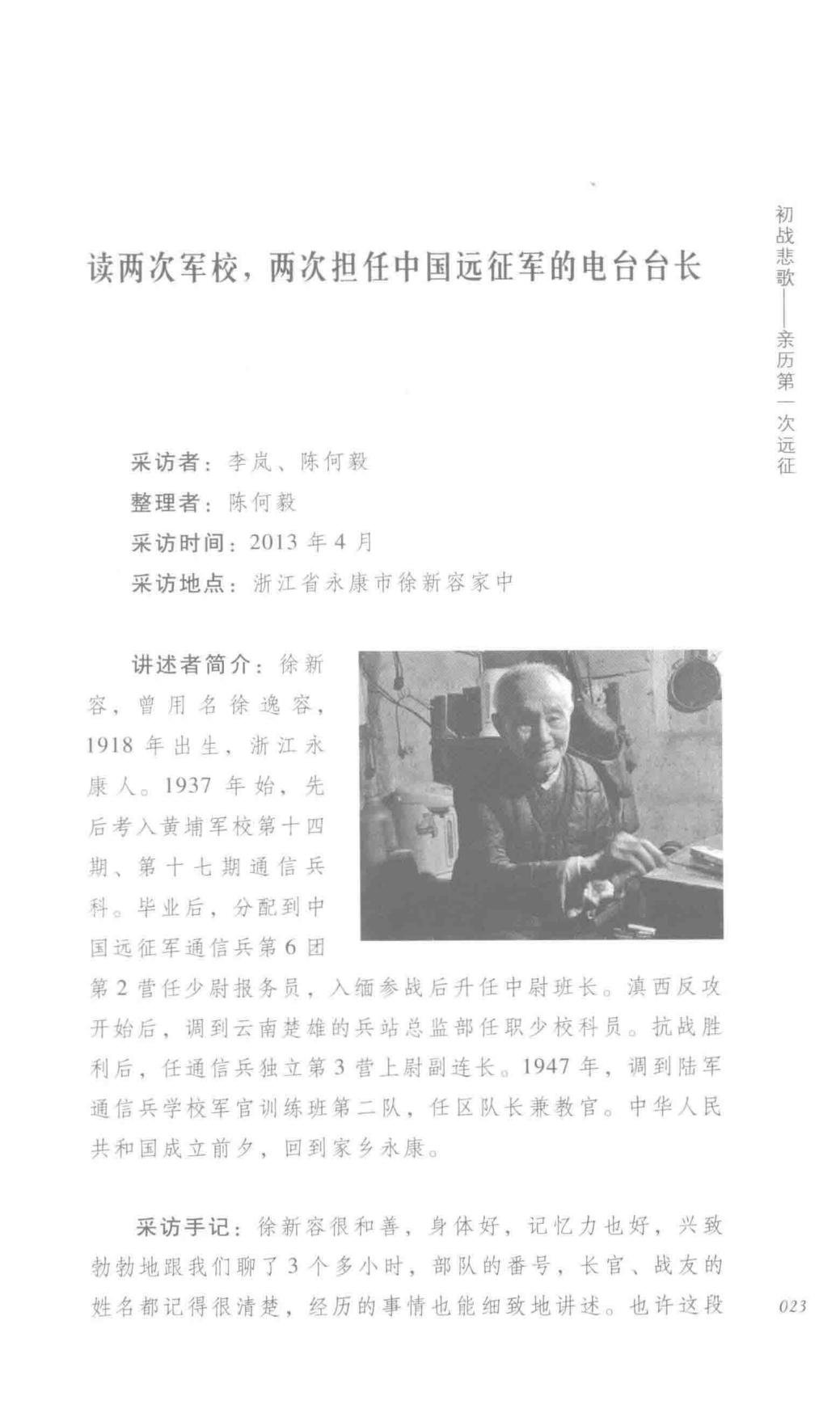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