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徐丽飞、刘小翠
整理者:于广、吴峥嵘
采访时间:2012年11月14日
采访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讲述者简介:程绍颐,1921年8月出生,安徽潜山人。1942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十七期步科,后又进入机械化科深造。1943年年底毕业后,被分配到昆明第5军司令部担任汽车队中尉排长。1944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在龙陵第9支部任参谋。1949年,在四川双流起义,后被分配到南京某中学任教,直至退休。
采访手记:采访程绍颐那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来到老人家时,老人给我们开门后,马上又坐在电视机旁,转过头来跟我们说了句:“我们先看看电视,待会儿再聊。”
几分钟后,老人终究觉得有怠慢我们的嫌疑,将电视声音调小,转头讲述起自己的故事。聊起日军的侵略暴行后,老人忘了电视的事,满是愤慨地说起日军的各种恶行。对于老人来讲,这种仇恨是铭记一生、无法忘却的。
在老家做救亡工作
原来安徽的省会是安庆,我在安庆读中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庆让鬼子占领了,立煌变成了当时安徽的省会,就是现在的金寨。为什么叫立煌呢?因为卫立煌是国民党的军官,国民党打共产党的时候,是他把这个地方打下来的,所以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日本鬼子打过来后,学校就撤退,我没地方读书就回家了。我家在大别山南麓,是务农的,可我不愿意在家里种田。我就往后方去,可平汉线(北平到汉口)给鬼子占了,我就又回来了。
当时全国有个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地下党领导的,负责人是周新民,目的是团结大家一起抗日打鬼子。县里也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我就在那里当秘书,做救亡工作。我们没有补贴津贴,只管饭吃,穿草鞋,穿简单的衣服。我还参加救亡工作团第32团的救亡活动,在棋盘乡工作一个多月,领导动员群众抗日支援前线,反攻安庆。
反攻安庆要经过一座山,需要偷袭安庆前面鬼子占领的一个据点。我参加了这次战斗,是作为政工人员参加的,政工组长是个女同志。那天傍晚,大家在潜山县的河滩上集中,说晚上要夜行军,一个跟一个,不准打电筒,不准有点光。后来鬼子逃到安庆城里去了,我们算是胜利了。
崎岖的入学路
后来,我看到军校招生的广告贴出来了,上面说一经录取,一切费用由国家承担,还有毕业后就是少尉,我就去考试了。在县里初试考语文、政治、外语、数理化,比较简单的。在省里复试时,还是考语文、政治、数理化、英语,比县里深一点。我们有好几个人去考,就我一个人被录取了。后来弄黄埔同学录时,看到好多安徽的。
军校的主任是胡宗南,他的个子比蒋介石矮,副主任是周嘉彬,还有一个副主任叫罗历戎。周嘉彬是张治中的女婿,新疆和平解放的时候,他是立了功的,这些人现在都不在了。当时考军校都是要17岁以上的,还要求身体健康,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视力要好一点,没有抽血这些项目。我们没有分正取生、备取生,我去的时候就被分到步科第九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军校除了步科还有炮科、工科,我有个好朋友考到炮科。
后来,西安那边让我们从安徽立煌走过去,通过河南,一天走个四五十公里,走到一个镇上就歇息。有的人脚都起泡了,晚上用水泡过后还得走。路上遇到人问还有多久到镇上或村里,他们就说“一泡”,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一泡尿的功夫,就是快到了的意思。
就这么走着,有天差点被飞机炸死。那是我们从洛阳过潼关坐火车的时候,在火车站附近有一个洞,洞的外面有个门,门上有个链子,我们大概有11个人在洞里面。突然,鬼子有飞机来炸中正桥,还有火车站。结果炸弹炸起来的风把这门“咣当”关上了,里面有好几个人哭了。哎呀!我脑子里闪过一念,不会死在这个地方吧?结果一睁眼,人都还在。
刚上了到渭南的火车,鬼子飞机又来了。我们就赶快下来,它扫射的时候我们就趴到火车底下。那时的火车是铁皮的,门一关起来,都快闷死了,最后洗澡时,身上都长虱子了。在潼关这个地方,对面就是鬼子占领的地方,所以我们偷偷地一个一个手牵着手过去的,要是让鬼子知道了,马上就打过来了。
在军校里,我养成吃饭快的习惯
在步科的时候,一天的生活就是吹哨子起床,吹哨子吃饭,“起立!开动!”这样的,所以我养成吃饭快的习惯。晚上睡觉有查房的,不能晚睡,也不能夜不归宿,否则要关禁闭的。天一亮就吹哨子起床,然后跑步,跑完后吃早饭,然后上课,上午上课,下午出操,晚上在一起唱唱歌、拉拉歌,生活单调。我们星期天可以进城,去理个发,吃个羊肉泡馍,那时候没什么钱。
到军校后就发衣服,都是布的,袜子也是布的。在军校用的枪是汉阳造,都是三八盖子的,老把势。学习的时候没有好枪给你用,好枪都拿到前线打鬼子去了。那时候营养也不够,我们经常吃小米,很少吃白面馒头,只有你生病了才会给你发一点大米。
学科主要学政治,有“总理遗教”,教政治的老师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除了政治,还学军事,如怎么操练、怎么进攻、怎么防守。训练是一个队一个队训练的,就是出操跑步、走正步、高低杠、跳马、打枪,趴着打,站着打,跪着打,卧着打。还有军事演习、对抗演习,搞对抗演习,是战术的,谈不上战略。没有学外语,学步科的时候没有,后来分科深造有专学俄语的,阿拉伯语、英语的比较少。
我的队长和同学,现在没见到一个
我们队长叫李甚严,毕业于黄埔军校,原来在部队当师长,我们说他是半部《步兵操典》起家。我们队有100多人,现在没见到一个。有一次,我看报纸看到区队长李长春,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报纸上说他被抓起来了,说他是特务。他是不是特务呢?这个搞不清楚。
我两个最好的同学,一个叫张一新,是绥远的,绥远后来划入察哈尔省,现在没有这个省了,我生病的时候他喂饭给我吃;另外一个刘伯森,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后来去了沂蒙山第74军张灵甫的部队。我到武汉住在阅海路13号,他来看过我。后来我给他写了很多信,寄了包裹,他都没收到,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也没找到。现在这两个人不知道生死,我们都92岁了。
“军善字122号”
我们当时凡是军校学生自然就加入国民党,是在毕业的时候集体加入的。有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到王曲的第七分校校本部照相,4个人坐一排,就成了国民党员,我的国民党党员证是“军善字122号”。
我们毕业的时候,蒋介石来了,宋美龄也来了。蒋介石还讲话,他讲一口浙江话,我们听不懂。当时已经是秋天了,我们在大操场上站着,还是穿着单衣服。毕业的时候,毕业证书、毕业佩剑、武装带这些都有,但没有同学录。后来我的这些东西都丢了,因为我用一个小皮箱装着这些,结果有一次坐车颠簸,都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到机械化大队深造
我是1942年7月从步科毕业,本来要分到部队的,但学校挑选一些文化基础较好又年轻的,继续深造,我就在西安又多待一年半。虽然当时我初中还差一个学期没毕业,但我一直自学,所以后来军校有外国教官,我好多都能听懂,还能回答问题,《一千零一夜》我都能背。考试的时候,分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还有特别炮兵和机械化这些科,我就用英语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教官很欣赏。不过还是要补习数理化,要不然汽车这些原理搞不懂。当时汽车是苏联的,坦克是意大利的,有3吨重、9吨重两种,我都实习过,但是没有上战场。
我选择并考取了机械化科,学大炮、坦克,所以我现在写简历又是步科又是机械化科。这个机械化科是史均瑶搞的,还有戴安澜,他的儿子现在还经常跟我们一起开会。在机械化科,我们主要学汽车构造、汽车驾驶、汽车原理这些科目。一开始我们也不会,由老师带着学发动机、油路、电路这些知识,所以我现在会开车。后来我到南京认识我老伴的时候,她住在宁海路13号,她有个家人在清凉山当连长,专门调一辆车过来给我开。我成天带着她、她妹妹和她父亲到处去玩,到玄武湖、鸡鸣寺玩。
在机械化大队的时候,我们衣服是军校统一发的,都是绿色的。衣服口袋一开始是两个,后来是4个。上课的内容有时会用到英语、俄语,比如讲到炮,就是俄语,有关英语一般都是汽车方面的。我们学机械化的时候才有外语教官,在步科的时候没有,教材也都是英语,有翻译,我们自己也能听懂一些。有个人叫苏必特,他是教英语的;还有个马志军,在机械化大队的时候是队副兼任我的外语教官。
坐飞机去第5军报到
1943年年底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昆明第5军杜聿明的部队。第5军在重庆有个办事处,我一开始住在重庆第5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有个女儿生了个小孩,她的妈妈有些小衣服、小帽子之类的让我给带过去。她老公就是汽车队的,让我坐飞机去昆明,我说我怎么够资格坐飞机呢?我刚毕业最多按中尉分配,他就给我写了上尉连长。这样我就够资格买飞机票,坐飞机两三个小时就到昆明。飞机上都是外国人,只有两三个中国人。同去的一个同学不肯坐飞机,他说他要游山玩水,结果遇到翻车死了。
我到第5军司令部担任汽车队中尉排长,主要是运输物资,待了不到一年。记得有一次,我还开车跑到曲靖。在曲靖到昆明有辆小火车,小火车烧木炭的。龙云是云南王,他用的铁轨是法国的,跟普通的不一样。蒋介石怕他搞独立,就派了杜聿明去监视他。后来蒋介石又把龙云弄到南京去监视,最后龙云还是跑了。
在龙陵看油管
卫立煌当司令长官的时候,我就跑到中国远征军去了。卫立煌是我们老乡,当时大家就说去他那边,好多安徽人都去了,我也跟着去了,第5军还说要通缉我。在保山的时候,我在那里负责收粮记账。那时很多老百姓送粮送东西,有的拿车子推,有的用骡马送,有的用肩挑。后来我到了龙陵,因为我有个同学在第九支部,他爷爷在第九支部做支部领导,我就去那里当参谋。
那时候美国人铺了中印油管,把油从印度和缅甸输送到昆明。100多里的地方有个加压点,有时候吐油、漏油,不得了的,油山火海。所以我们负责在那里看管,哪一段油管漏油了,就马上关闸。我在龙陵的几个月主要是看油管。
差点接受军事审判
日本鬼子投降那天,大家特别高兴,像热水开锅了一样,中国兵、美国兵都鸣枪,老百姓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龙陵负责接收,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可接收的。后来,我们回到昆明的时候,沿途看到鬼子老实得很。鬼子穿着黄军装,没领章,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喊他推车子,他就乖乖地推车子。
有一次,我带5辆汽车从芷江送青年军到长沙,我坐最后一辆。前面的司机和副驾驶员一起做坏事,带黄鱼,就是搭客收钱。后来我们从长沙回芷江的时候,我拿枪对着山开了一枪,那时就感觉是不祥之兆。后来路上有一辆车翻到山底下了,开始也不知道死了几个人,把车翻过来才发现死了3个人,当时就地土葬了。我还从小镇上找人来照相,因为当时我们没相机的。有个广东人,他说这个车现在修不了,我们把重要的零件像引擎、电机、轮胎这些卸下来带回去。
当时,我们团的团长和副团长不和,闹矛盾,而我是团长的学生,所以副团长就借这个机会找别扭,说我损坏公物。团长没办法就把我关禁闭一个月,还要接受军事审判。我的营长姓钱,人很好,他同情我,来看我,后来我没见过他了。最后,我就把照片、写的材料拿出来,他们叫我回家,我说不回去,好马不吃回头草。有一天,我去街上理个发,吃点东西,碰到了熟人,他说:“怕什么!走,回南京!”之后,我跟着团长到了南京,成立短期训练班。
最后一次“总理纪念周”
在南京的时候,政治部说短期训练班要裁撤,成立教官训练班。我就去了联勤总署,负责军事补给方面的,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到武汉成立了运输学校。在武汉,我结婚成家了,又跟着运输学校一直到四川的双流。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到遵义,解放军第二野战部队打来了,从湖南追过来了。我们在桐梓,就是靠遵义那个地方,做最后一次“总理纪念周”,以前我们每周一都做的。校长叫黄振,后来有个大使也叫黄振,但是不可能是他。他很伤感地说:“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总理纪念周了。”
那时,人心惶惶,东西卖得便宜,猪肉一毛钱一斤,稻子一块钱一担,相当于七八十斤稻米,便宜得很。
在双流起义,在南京教书育人
1949年,我们在双流起义,我就被分配到西南军区总医院当文化教员,搞政治宣传工作、协助演话剧等。我没回安徽是因为很早失去联系,而且当时我岳父在南京是检察院检察长,地位很高,他的房子比较宽敞,他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就去南京了。本来我准备去抗美援朝,但当时肺部有点不太好,就没去。
后来,我被分配到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当语文老师。第三女子中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变化很大,男娃儿也进来读书,那时不叫第三女子中学,叫井冈山中学,现在是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第三女子中学很大,把第六中学、第二十二中学也合并到里面了,现在我的关系就在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324-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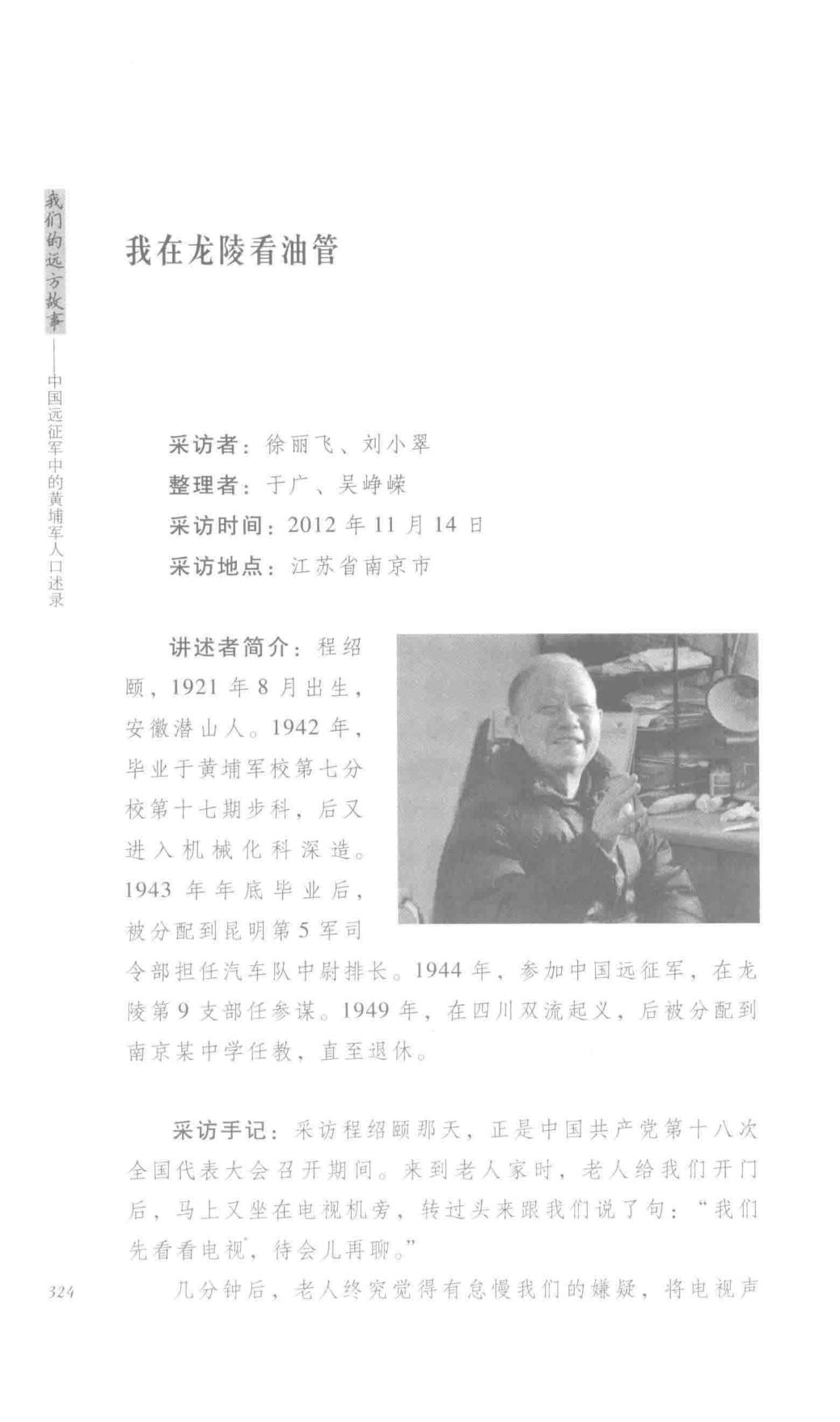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