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李岚、杜穗红
整理者:李岚、白廷兵
采访时间:2013年1月
采访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谭延煦家中
讲述者简介:谭延煦,1919年出生,广西桂林人。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第十七期。194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第11集团军总部当见习参谋,后又到“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干训团”)任学生总队区队长。半年后,加入到11集团军直属团参加中国远征军作战,先后任排长、代理连长等。后到第71军预备第2师任营长,参加过高黎贡、腾冲等战役。抗战胜利后,任第93军第278师工兵连参谋长。1949年,在云南昆明起义。
采访手记:谭延煦是我们到桂林采访的第一人。老人虽然已经94岁高龄,但思维仍非常清晰。他曾作为预备部队参加腾冲战役,也曾越过历经惨烈激战拿下的高黎贡山。山顶层层堆叠的死尸和脚下踩到尸体时软绵绵的感受,到现在老人仍然忘不了。还有那攻破腾冲城后,城内满目疮痍的场面,他至今也仍记忆犹新。
老人现在没有退休金,没有经济来源,靠志愿者的照顾和捐献清贫度日,然而他对此却没有任何怨言。我们仍记得老人说过的那句话:“(那时)老百姓虽然生活艰难,但是精神是饱满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位虽历经生活磨难,但仍热爱生活的黄埔老人形象。
从桂林经湖南加入军校
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正值日本飞机每天轰炸我们那里,我们上课都已经不在学校里了,而是在老人山里上课。那时,我对读书已经不感兴趣了。从大道理上来说,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想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原来我的想法也是考军校的,但是我对分校不感兴趣,因为本校各种教学器材和设备更齐全些。
1939年高中毕业时,正好赶上本校在湖南招生,到桂林来贴招生广告。当时我和同学一二十个人都报名了,后来考上的只有3个。当时中国大部分领土都沦陷了,很多青年人跑到后方来,只要有工作、有职业的,都愿意去考。军校规定高中毕业、大学及同等学力的都可以去考,这个同等学力范围就宽了。当时参加考试的同等学力的多一些,因为在当时高中学力就很难得了。
考试的地点是在湖南祁阳。考的是数理化、语文之类的东西,考试纪律相当严格。后来我听说我们那批在湖南考的有9000人,被录取的有130多个。那些考学术科和体格不合格的,就让你回去,由学校给你回去的路费。只有考试合格了,才能入伍。
我们走路去成都,学校里派了两个带队官带队。大概每天走60里路,看路上住宿情况,起码50里路,多则70里路,原则上是60里路。路上有大的村子、圩镇,能够住下来,就在那个地方住了。我们用了差不多两三个礼拜的时间才到了成都,住在杜甫草堂。那时宿舍和教室全部是临时做的,上面是竹篱笆,下面拿草盖的,没有瓦。
我们是重点培养的一个总队
我被分到第十七期第一总队,教育长是陈继承,一个大队只有两个中队。抗战以后,每一期都有两三个总队,其中有一个总队是重点培养的,而且这些总队里纯粹步科的多。我们要进行起码两年半以上的学习,那些学了两年或者一年半的,在日本人投降、国家恢复正常以后,还要回来学校补课3个月。我们这些超过两年半的,就不一定回去补训了。
那时主要是干部缺乏,伤亡太大。当时有一种说法,军校培养再多当军官的学生,都不够死的。蒋介石对我们这个总队还是蛮看得起的,逢元旦、春节、校庆之类比较重要的节日,他都跑过来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个队算是素质比较高的一个队,里面大学生有一两百人,大部分都是高中毕业,同等学力的都很少,也就百八十个。
以劳动为主的预备入伍
我们进去以后是预备入伍,预备入伍和正式入伍都是基础教育。一天都是出操、立正、稍息之类的,我们也都习惯了,因为在广西的时候,我们从初中起就有军训了。像我们桂林中学,从初中一直到高中,都有军训教官,两三个班编成一个队。初中毕业以后,还在南宁武陵正式军训了一年。
在预备入伍阶段,我们还是以劳动为主。在草堂寺和青羊宫那一头有一条公路,预备入伍期间,我们除了早晚基础教育以外,吃了早饭就要出去修那条公路。那条公路挖下去起码有2米深,一层石头一层黄泥浆的铺路。预备入伍3个月后,正式入伍也是3个月。正式入伍是军风纪教育,劳动时间没有了,上课开始讲军事常识等。
我最先想学的是炮科
入伍期满以后开始分科考试,入伍时是在草堂寺,分科以后就到西较场了。那时我们兵种比较多,步、骑、炮、工、辎重、通信都有。我们分科跟那个考试分数没有关系,你要学哪一科就任选一科,比如说你要学英语就报英语,要学俄语就报俄语,你觉得哪样比较有兴趣、有前途,就学哪样,报了以后由学校来定。
我最先想学的是炮科,学校要求身高是1.7米,而我那时才1.66米。我和大队长讲了几次,他说没办法。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在高中时已经学过步科,在武陵又受了一年的军训,步科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学习了,所以报工科。
当时工科学习内容,讲得通俗些,就是“逢山开路,逢水搭桥”,比如架桥、筑城、挖战壕、做掩蔽、做各种枪炮的掩体,另外就是爆破、炸桥、炸敌人的堡垒等。我们的文化课教官一直到毕业时还有,数理化、语文、外语一直到毕业都还要学。普通科是普及型的,也一直有,主要是学战略战术等。每年我们起码要阅兵两次,国庆和校庆这两个节是一定要阅兵的。阅兵在军校也不算比较重大的事情,主要是看看学生身体怎么样,学习情况怎么样,了解一下。
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
入伍期时我们没有假期,之后星期天就可以放假休息了。一般是早上10点放假,下午5点收假。放假就是在街上逛逛,有些同学是四川的,或者在成都有熟悉的亲友,就去那玩一下。我一般逛逛公园,或者有同学邀请去看看电影。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些军校学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当时社会上对军校学生评价和看法形形色色,有些人觉得学生雄壮,身体蛮好。其他很特殊的,我倒没什么感觉。
我们的军服是黄色和草绿色的。夏季服草绿色,冬季服草黄色。放假出街学校规定要洗干净,划破了洞就打个补丁。有一套外出服,黄呢子的。有个圆形的领章,上面有“军校学生”字样,蓝底白字。当时胸口上有徽章,在左边,小口袋下面写: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哪一期哪个大队学生某某。
讲不完的军校伙食,“我们这是陪公子赶考”
关于军校伙食那就讲不完了。我们进军校以后,伙食就不好,特别广州、南京沦陷以后,后方好多乱七八糟的人搞鬼捣乱,我们这些学生比当入伍生的时候还苦。我们那时去买菜,那个芥蓝包、莴苣叶起码都有一半是黄的,只要没烂就行。
我们学生怕炊事班伙夫头在里面抠钱、揩油,所以每天都会派两个学生跟着伙夫头去买菜。伙夫头是军校长期雇来的,做了十年八年的都有,除非是犯了错误开除。他们和外面卖菜的比较熟悉,经常打交道。其实,我们和他一起去买菜也就是做个样子吧,真给他自己去买还要便宜点,比如一块钱买10斤,他去一块钱可以买11斤。所以,我们同学说:“我们这是陪公子赶考”,陪着去罢了,你要是去管他,还买不到那么多呢。后来就让他自己去买,我们挂个账。
有一段时间,我们那个队的学生,突然一下子有二三十个人,到傍晚黄昏时,眼睛就看不清东西了。医生检查,就是吃莴苣叶子,油水太差,那时一斤油100多人吃一天,规定吃三餐。早上吃稀饭,或者煮点面疙瘩吃,中午吃一餐,晚上又吃一餐。一餐才二三两油,买的菜又是像给猪吃的那样。
其实,我们的伙食费并没有少,只是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那时社会秩序比现在乱得多,老百姓要涨价,谁也管不了它。现在还有工商等单位来管,那时没人管,虽然有个商会,但是商会徒有其名。
偷吃花生的经历
我不太喜欢跟人家讲话,搞活动也少参加,看电影都很少有一次。星期天放假,我有个习惯就是去外面买花生吃。那时从西较场门口出去就有一条护城河,是清朝时保护城池而建的,也就一丈来宽。过了河上的桥,对岸四川人卖食杂、花生米的很多,这个在我们广西是没有的。那个簸箕很大、很圆,堆起来的花生是没壳的、炒好的那种,我就出去买一斤装在口袋里。那时我们规定在街上是不准吃东西的,我就一个人或者跟两三个同学一起,到公园里去,那时成都的公园也流行泡茶聊天。我一个人可以吃完一斤花生米。晚上回来再买一斤,留着偷着吃,有时候我在床上也偷着吃。
区队长要求还是很严格的。我们衣服的4个口袋都是规定了应该放什么东西,比如这个口袋装笔记本,不能乱装,他第一次纠正你,第二次就处罚你。不过这在入伍期最为嚴格,纯粹是军风纪生活,升学以后反而没那么严格,区队长和队长把道理讲完就看个人自覺了。而在入伍生那时,真的是官是官,兵是兵,非常嚴格。我偷吃花生的时候,同学之间也没有告密的,我们基本相互理解,没有什么嫉恨。学生们也都很遵守纪律,我从入伍生到毕业,在学校没见到有抽烟的。
我们对党派没什么感觉
在军校里,我们对党派没什么感觉。我们正式入伍以后就集体入了国民黨。那时入党也只是个名义,党员簿上有你的名字,什么活动都没有,党费还要交,每个月到时间,队长就从我们工资里扣收党费就是了。我们预备入伍是二等兵,正式入伍是一等兵,分科后是下士,学校根据这个等级给工资。
我是1939年10月到11月间进军校,到1942年夏天毕业。毕业时,我们发了同学录,还有佩剑。佩剑是去队里去领的,它上面有一个歪皮帶(军人帶)。佩剑上面一面写着:中央军校哪一期哪一个总队,另一面写的是“蒋中正贈”。现在想起来,那个佩剑上应该有编号,比如你这个总队有1000人,编号就是1到1000号,不过上面没有刻名字。我们还有一个军校的毕业纪念章,不过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纪念册也都丢了,纪念册里面是些相片,和同学录差不多一样,大小不同罢了。
分配时,我算是运气好的
1942年毕业以后,我被分到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宋希濂。当时我分配过去以后,好像都没有认识的同学。其实他们都是直接分到部队去的,到后来我当了中尉、上尉,活动能力比较宽了,才发现大家很多都是一个总队过来的。我们被分配时,学校先给个通知,预计几天能到部队,按当时的车费和伙食费给钱,有报到期限的。我在报到之前,回家休息了几天。
分配时,我算是运气好的。刚去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人家就说,你到参谋处工作吧,我就到了总部当见习参谋。我们参谋处分4个科,通信、交通、作战、情报。我是在情报科负责搜集战况,包括搜集汉奸信息或者社会有无扰乱情况等等。我刚去时,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收集战况,后来干了一段时间,才慢慢知道。我也不懂怎么写行文,我们参谋主任人很好,告诉我对上面行文怎么称呼,对相等的、对下面的怎么写,这样自己慢慢学,才学到一些。
负责带学生的干训团区队长
当时国内很多学生青年和回来的华侨青年都流散在外面没有工作,宋希濂就想把这些有青年收容起来,在大理成立中央干部训练团。招生广告我见过,虽然名义上要求至少小学毕业才能入校,实际上只要认识1、2、3,都可以进去。虽然也考试,但也只是个名义罢了,并不严格。主要目的还是收集在地方上的流散青年。我在参谋处没多久,半年还是几个月吧,就去学生总队负责带学生。刚去时,我是少尉区队副,后来升到区队长。
干训团的训练与军校的组织形式是一样的,也是分总队、大队、区队。教学有些也类似军校,但是没有在军校要求的那么严格。教育长宋希濂也不经常来,有时候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就来看一下,一般个把月来一次。另外有一个副教育长负责,是总部派来的,少将军衔。我们的总队长也是个少将,黄埔军校第三期还是第四期的,记不清了。干训团也没有分科,一直以步兵为主。学习时间半年左右,毕业后主要分配到第11集团军,别的地方人家不会要的。学生有的分到部队带兵,有的在部队或者什么单位搞政工。
对宋希濂的印象
我在那边工作一直到学生毕业,大概有半年时间,后来我被分到第11集团军直属团。这个团是后来组建成的,主要是训练士兵。原本是宋希濂想扩充自己的警卫部队,但是他已经有警卫营了,在编制方面说不过去,只能暂时以集团名义成立这个组织。宋是湖南邵阳人,他的警卫营里面的军官和士兵大多是邵阳人。讲个笑话,晚上过了9点以后过路要问口令,他就“嗯啊嗯啊”的。邵阳有个特殊的口音,鼻音特别重,不管用什么口令都好,只要“嗯啊嗯啊”的,就晓得是警卫营的了。
对于宋希濂我没有接触,不过他的生活情况我还是了解一些。因为他的副官和参谋是我的同学,大家遇到的时候,就会时不时爱聊一下他。我最初见到宋希濂时就觉得蛮特别的,30多岁,佩着中将的金牌牌,头用油梳得亮亮的。那时我个子小,大家开玩笑,说小鬼我们换一下,我说怎么换,他说我下部队,你来服侍老总,我说你在这不舒服吗?日晒不着雨淋不到,出去陪着老总,不是车子就是马,又不用走路,还不舒服?他说不舒服,你跟着他,去哪都去不了,他去开会或者干什么的,你要在车子边或者附近等着他,等他开会、视察回来,看不到你,就要挨批评的。我说我不行,侍候人的事我干不来。
换美式装备后,翻越高黎贡山
刚去不到一个月,我们那个连长被派到昆明学习美国装备的新武器,我这个排长就开始代理连长。当时我们还没有换发美式装备,还是七九式的步枪。后来陆续装备美式装备,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记得开始大反攻时,我们团长穿一件美国雨衣,其他营长、连长、当兵的,个个都是一件斗篷,拿纸、油漆、竹子编起来的那种。第71军第36师也没有太多美式装备。
在大反攻前,日本人过了高黎贡山,到怒江边,情况相当危险。我们与日军隔着怒江对峙,第71军死守在这一边。在腾冲已经打了两三个礼拜后,我们部队才加入战斗。从保山这边出去,花了三天两夜强行军,过了高黎贡山才停下来,一直没有休息。
高黎贡山海拔四五千米,人走到半山腰,日头还没落,天还没黑,看到上面有太阳,半山腰下面下着蒙蒙雨。我们先在山脚吃饭,因为如果在山上煮饭吃的话,带柴火上去,都会变成湿的。我们刚到时天有点黑,等于现在六七点钟。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那山顶起码有两里长的路上,死牛、死人、死马堆了一大堆,踩上去软软的,有的生了蛆,有的只留下些枯骨头。天黑了,走到什么地方,踩没踩到也不知道了,一路过去都跌跤,我们连里士兵跌过跤的超过半数。山上面是黄泥浆,到腾冲时都跟泥猪一样。日本人那时装备好些,都拿汽车拖引,所以就在高黎贡山修了一条马路,是一条很窄的路,骡马、单人可以过。
腾冲战役中的预备队,没有什么怕死之类的顾虑
到了腾冲以后,我以为会马上进入阵地。结果到了离腾冲还差5里路的时候,上面说停军待命,也没说什么任务,就是待命。开始我们以为情况紧急,马上要投入战斗,连我们团长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说要看前方部队什么地方吃紧,或者缺人员的话,我们就补充上去,另外也怕日本人跑出来。
那时腾冲攻城部队死伤相当严重。到腾冲可能有半个月,一直等。日本人在城里待不住了,东西吃完又送不进来。有一次,10多架日本飞机飞到腾冲,那时我们防空力量差,保山有陈纳德的飞机队在,我们得了情况立刻通知他们。大概过了20分钟,日本飞机还没到腾冲城上方,就看到陈纳德的飞机到了。有些不要命的敌人就把东西投下去,城里得了1/3,大部分投在城外,粮食、罐头等都给中国军队得了去。日本飞机逃命要紧,顾不得那么多,陈纳德的飞机也不去追他们。
在腾冲战役中,我们虽然没进入战斗,但是也在战斗系列里头。上面有命令就要随时准备战斗,也不知道哪个部队需要补充,不一定是一个团去补充,也可能是缺一个营、一个连,我们就补充上去。我们当时讲笑,干脆早点上火线,打死就算了。无论是当兵的还是当官的都不怕死,现在窝在这里,就是耐不了这个烦,死不死、活不活地等着,莫名其妙,精神特别不舒服,还不如干脆上前线。
中国的士兵,战斗思想和战斗精神其实是很旺盛的。
虽然我们部队不在第一线,可我同学多,我经常去第一线找他们玩,我有好几个晚上在凌晨以后跑到他们那儿去。凌晨两三点钟,这段时间是最安静的,没有枪响,偶尔有枪响,也像小孩子放鞭炮一样。我们预备队和前方部队也就距离一两里,我们下象棋、打扑克,就跟平常一样,大家都没有什么紧张、怕死的。那时的战斗情绪你想不到的,在第一线没有什么怕死之类的顾虑。
腾冲城破后,他死的不值
腾冲城破以后,我们就去清扫战场,有10多天。我和我们连的一些士兵、干部进去里面看了一下,里面很惨,鸡、狗都没有了,房屋和树木都烧焦了。当初估计腾冲、龙陵有一次战役,就提前疏散老百姓,老百姓倒是伤亡不大。中国军队死得多,日本人最后就剩一个。那时听上面战略方针,一是防止在印缅边境的日本人往中国撤;二是防止中国腾冲、龙陵、松山的日本人在中缅边境的腊戍会师,一会师他们兵力就强大了。所以,无论龙陵也好,腾冲也好,都不准一个日本人跑出来。
我记得预备第2师有一个团的团长,他个子比我矮点,也是湖南人,带了1个警卫排和3个营在腾冲城里。当时敌人那边还有一个日本人没死,从城墙的枪眼打了一枪,就把他打倒了,正好打到头上。后来说他这个团长死的不值,我们把日本人打垮了,他却被日本人打死了。
我们直属团作为后备补充部队基本上没什么伤亡,伤亡都是病痛的多。之后,各个部队由上面指定到什么地方驻扎,等于是整训一样就地休整。我们部队就回保山,我们那个连在保山守卫飞机场。
随身带着“鸦片烟”
在战场上,我们医药缺乏,云南瘴气又厉害。到了怒江附近,老百姓说,你们外头来的人,要抽点烟。我们这个地方瘴气严重,得了瘴气,是没有药整的。我当时带着烟,自己不抽,给别人抽,听了老百姓这么说,我也抽起烟来了。
在怒江那个地方蛮多神话的。老百姓说,你们口干了不要喝江里的水,那个水有毒的。有一次,我口干得不得了,等我们连的兵过了,我在后头走到河底下捧了几口水喝。那个河又深,走下去起码二三十米。我那时身上都带着“鸦片烟”,不是真正的鸦片烟,是烟杆里的烟屎,把它挑出来的,拿个瓶子或者纸包着。那个蛮有效的,拉肚子、感冒,吃了特别灵,没有开水,用冷水喝下去,我的挎包里随时都有半把斤。
那时野战医院离得远,药又缺乏,得了感冒什么的不好治就等死。特別是在云南,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发高烧,人发高烧,就好像疯子一样,那个架子床一米多高,他都有本事跳到那个上面去。当时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我给他吃点我带的鸦片烟,效果不大。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年纪轻,社会常识差,分析不出来。当时只有社会上的草药医生,请来看了一下。病刚发作的时候,还有办法把烧退下去,一发到高烧时,他也没有办法了。由地下一跳到架子床时,那就没治了,高烧发热已经到了顶点。
战争是不好的东西
日本投降的时候,我们还在保山守衛飞机场。云南没有进行什么受降仪式,在越南有一个受降点,云南省主席卢汉去搞的,我们部队也去了。那时我们的广播很少,电视也没有。听说日本人投降了,我不太相信,想当初日本人都从东北打到西南,半个中国都没有了,他们怎么会投降呢?后来确认是真的投降,无论城里还是乡村都放鞭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兵都是一片欢呼,场面相当感人。这时,我才相信日本人是真的投降了。对于战争,虽然不说有什么意见,但总觉得相当难受,战争毕竟是不好的东西。
我在保山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945年日本人投降以后,第11集团军还存在,到1946年中国远征军撤销,宋希濂去西北当了西北行营主任,第11集团军就不存在了。
我跟士兵关系很好
虽然我是一个穷光蛋,但是分外之财我不取,我有自己的原则。那时我对士兵蛮好,我本来当连长有82块钱,用不完的,家里又没负担,自己也年轻,想着士兵们没烟抽,我就每个班一个月发一两斤烟丝给他们。他们衣服烂了就让一个班买一个针线包,给他们去缝。因此,士兵对我也很好。
那时,我们吃饭就跟打冲锋一样,而我不管在哪个部队都没有这样过,我都保证他们能吃饱。一个人的肚子有多大量,尽着他们吃,今天不够吃,就拿明天的量来补,明天不够拿后来的补。这样一个半个月下来,煮点粥给他们吃,也吃不去多少了。我那时也和他们一起吃,不像人家说的,当官的另外开伙。无论我在哪个部队,都是让大家一起吃。那些士兵开始两天会抢着吃,看到不抢饭也不会挨饿了,他们就不抢饭吃了。如果抢的话,一连一百多口人,一人多抢一口,都不得了。看到饭快没有了,立刻煮一锅出来,吃多少舀多少,大家都不再抢饭吃了。那些饭就能剩出来,一人一天一斤半米,吃不完的,如果抢饭吃只会越抢越厉害,吃多少也没数。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P228-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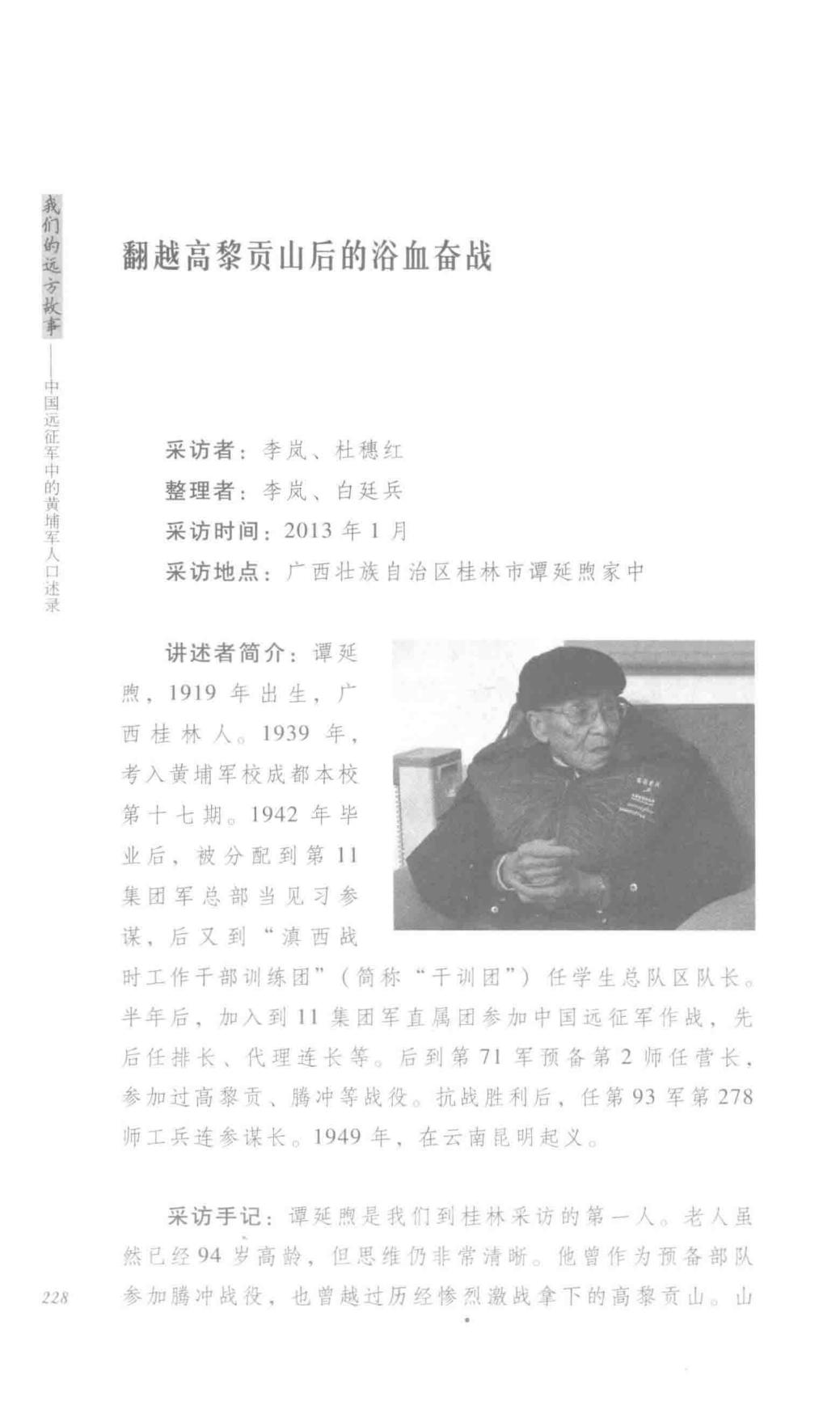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