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李岚、陈何毅
整理者:李岚、陈何毅
采访时间:2013年4月
采访地点:浙江省台州市
讲述者简介:王凯,曾用名王永华,1922年出生,浙江台州人。1941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八期步科第二总队第六队。1943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第二补训处任少尉排长。1944年,编入中国远征军第71军第88师,参加松山战役,后在龙陵与日军作战时负伤。抗战胜利后,分配到巫家坝机场守备团,后被编入第26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家乡台州。
采访手记:从采访开始到结束,王凯一直用着极快的语速跟我们聊天,似乎跟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他给我们描述在战场上与日军交火的情形,就像是在说昨天的事情。说到紧张的时候,他还经常站起来给我们做示范动作。老人还告诉我们如何根据子弹的声音来辨别子弹与自己的距离,让我们好像走进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明白枪林弹雨中的切身感受。
最后,老人告诉我们,他今年92岁,这一生很难得,经历过很多事情,有坏的也有好的。人生本来就是要自己深深地体会,要乐观面对一切,笑对每一天,才能让自己过得更舒心。
从黄岩中学考入军校第十八期
1941年,我在黄岩中学读书。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学校没法正常上课,只好搬到西乡的临时学校里继续上课。但是,日本人的飞机又追到西乡来轰炸。我意识到这书是读不成了,宁愿去部队当兵,也不愿在家当亡国奴。于是,我瞒着父母,跑到江西上饶去考黄埔军校第十八期。
入学考试要考国文、物理、化学、英文等科目,还要经过体格检查。虽然不用面试,但是我觉得体格检查的时候,可能也有些面试的意思。录取后,由于火车已经被日本人炸光了,我们就从江西桐城一路步行,先走到湖北宜昌三斗坪,又步行到重庆,再由重庆步行到四川成都报到。
在军校,每个人可以填报自己喜欢的专业。经过分科考试后,军校会根据成绩来分配。如果报了专业但考试不及格,就全部分配到步科去。我选了步科,是学迫击炮的。当时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开始是陈继承,毕业时换成了万耀煌。
在南校场受训,总队长王化兴,他是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区队长是王庆华。
在军校里主要是学军事学,就是学怎样打仗,枪和子弹怎样用。还有普通学,包括数学和外语,都是由华师大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任教官。一个礼拜学数学两个小时,外语也学两个小时,有英文、俄文、德文、日文,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学。我以前在学校学英文,所以我选了英文。军校还发了《三民主义》和《领袖言行》这两本书,读这两本书就算是政治教育了。由军训处处长邓文仪负责,后来又调来一个肖赞育。
也许我们是黄埔军校最苦的一期
在军校的生活很苦,吃稀饭只给几分钟的时间。烫得受不了,只能把碗转着吃。哨子“哔”的一声,不管你吃饱没吃饱,马上放下筷子跑去集合。我想我们这期应该是最苦的,连饭都吃不饱,家里寄过来的钱都买面条吃了。在南京军校有四菜一汤,我们连个浓米汤都没吃到。在饭里面还经常掺沙子,说是要训练我们刻苦耐劳。总体来说,军校第十六期之前生活都很好,第十七、第十八期都不行,第十九期也是苦的。
入伍生的6个月,是没有休息时间的。成为正式的学员后,每个礼拜天休息一天。每个月军校有津贴,也就几毛钱,根本不够用。到了休息那天,我们拿着家里寄过来的钱上街吃馆子,然后就回学校了。生活用品都是军校发,衣服、袜子、布鞋都是军校的。毕业以后,还发一套新的棉军装,过去发的都是呢军装。可能当时国家没钱,我们这一期就只能发棉军装了。
在毕业前,我们还进行了有攻防对抗的野战演习。在演习地段范围内的农作物,军校都出钱买下来了。我们第十八期是攻方,补训总队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期是守方。演习开始用的是空炮弹、木子弹,后来用真家伙了。这样一来肯定是有伤亡的,教育长怕负不起这个责任就下令停止了。
1943年毕业,我结束了两年半的军校生活。毕业时,军校发了好几个纪念章,军校纪念章、总队纪念章以及自己小队的纪念章,还发了同学录和佩剑。毕业以后向东边走的,学校用车子送到重庆;向西北走的,送到宝鸡。旅费算算多少,给你带走,不能多发,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
从第二补训处到滇缅战场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重庆第二补训处,任少尉排长。补训处主要负责重庆江北的警备任务,我在补训处负责训练新兵。1944年,滇缅战场需要大量的兵源,我们整个补训处编入中国远征军第71军第88师,军长钟彬是广东人。
补训处很多官兵听到要去缅甸前线打仗,都不愿意去。很多都偷偷溜走了,也就是我们这么傻,愿意去。第二补训处处长胡朗,是温岭人。上面要求交兵到中国远征军,他交不出来,因为兵跑光了。结果他被蒋介石关到陆军监狱,关了6个月,听说后来放了。
胡朗叫我带一连人去,还指定我当连长。我说我是排长,你给我当连长,我下面的排长没有怎么办。他说你可以指定几个资格较老的上士班长当排长。于是,我带了一个连的人从重庆机场坐外国的飞机到云南保山。到了第71军,事情曝光了,我还是当回排长。
我们没有马上投入战斗,在保山训练了3个月,我也当上中尉副连长。主要学习如何使用美国的新式武器装备,如火焰喷射器等各种武器,由美国教官来教我们。装备也都换成美式的,穿的皮鞋都是美国货,待遇好得很。受训3个月以后,开赴前方,在前方吃的都是干粮,牛肉干、香烟、口香糖等什么都有,每人每天一包。部队送饭的上不来,我们就吃干粮。
印象最深的就是松山战役
在中国远征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松山战役。我军和日军隔江对峙,他们在西面,我们在东面,两军对峙僵持。1944年8月,我们这些新兵源补充进去后,才又开始打松山。松山战役是由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负责进攻。友军有第8军,何绍周的部队。曹立德是台州椒江人,是第8军的,他也打过松山这个地方。
由于敌人的工事实在太厉害了,我们久攻不下,用尽各种方法。我们组织敢死队,三四个人一组,背着火焰喷射器,摸黑划着橡皮艇渡过怒江,跑到日本的阵地里面去,摸到日军的攻击死角。敢死队在出发前已经跟指挥部联系好,用信号枪发信号,绿色是怎么样,红色又是怎样。炮兵、空兵也配合好,各个兵种同时发动攻击。敢死队负责近距离攻击,顺着日军的弹道用火焰喷射器攻击。火焰喷射器相当厉害,喷出的火焰温度很高,对日军杀伤很大。
松山战役足足打了一个多月,原本郁郁葱葱的山林,经过飞机的轰炸和炮火的毁灭后,只剩下黄土了。双方战死的士兵漫山遍野,胜利后这些士兵的尸体都被埋葬了。这算好的了,有的时候打了败仗,部队一撤退什么都顾不上,很多战友连骨头都没有了。整个松山战役中,我们一天换了5个连长。其中一个山东人,个子高高的,姓汪的。我说:“你的个子太高,日本人的狙击手专门打指挥官的,一枪打过来就死一个人。”他说:“老王,怕什么……”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日本人从背后打过来。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还是挺提心吊胆的。随着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生死也见惯了,人就自然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子弹从头上飞过,我们可以从子弹的声音就能判断距离。如果子弹的声音是“哗、哔、哔”,那还远着呢;要是“嘘、嘘、嘘”,距离就很近,就要小心了。
在龙陵,我负了伤
攻下松山后,我们趁势直扑龙陵。在龙陵,我们和日本人在外围作战时,我受伤了。当时,我正在冲锋准备攻击目标,一个手榴弹打过来,我的腿一阵剧痛就晕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勤务兵把我背送到团部,然后团部派人送我到师部,师部再用吉普车把我送到保山第37兵站。
到了医院检查后,发现情况很不乐观,炮弹碎片卡在大腿和盆骨之间的骨头里。中国医生没办法,美国医生主张把腿锯掉。院长是浙江张田人,和我是同乡,对我很好。我跟他说:“锯掉了,我就剩一条腿,残废了,能尽量给我治吗?实在不行再锯。”院长把我的想法跟美国医生说,他们同意给我治。医生先把我的骨头取出来,把炮弹碎片拿出来,再塞了些东西进去,再把骨头接回去。手术后,我的整条腿都绑着绷带,医生每隔一个星期就来检查一次。我的这条腿总算是保住了。我在第37兵站养伤,一直到抗战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路走回家
中国远征军撤销后,很多军官退伍了,我被分配到巫家坝机场守备团,后来又编成第26军。解放战争时期,第26军撤到滇南。解放军来了后,把我们包围了,我们最后只有投降。接收后,士兵有的回家,有的被编入解放军部队。没有学历、资历的都是排长级别的,解放军也接收过去。剩下我们这种黄埔军校毕业,有学历和资历的,要接受3个月的培训,思想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家。
受训3个月里,大家集中一起上课。解放军接收了我们的武器不会用,还叫我当了3个月的教官,教他们怎样使用这些武器。到了可以回家的时候,国家按规定发给我们路费,一宿两餐,沿途还可以补给。拿着发给我的遣散证,沿路就可以通行了。
我是从云南到浙江,汽车不能坐,火车可以坐,一天走30公里,走3天休息1天。到了住招待所的地方,凭遣散证报到,晚上就可以在招待所住宿和吃饭。第二天有早餐吃,还发8毛钱的中餐费。这时,我就深深体会到共产党政策好,不用钱可以一路走回家。我先走到衡阳,再坐火车到株洲,株洲转车到杭州。从杭州步行到黄岩,总共320多公里,山路没通,都是小道。从杭州到金华走永康,爬过苍岭,到仙居走黄岩。单是从金华到黄岩就要5天时间,几百公里就这样走回家。到家的时候,我就只剩下一条短裤和腰带了。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271-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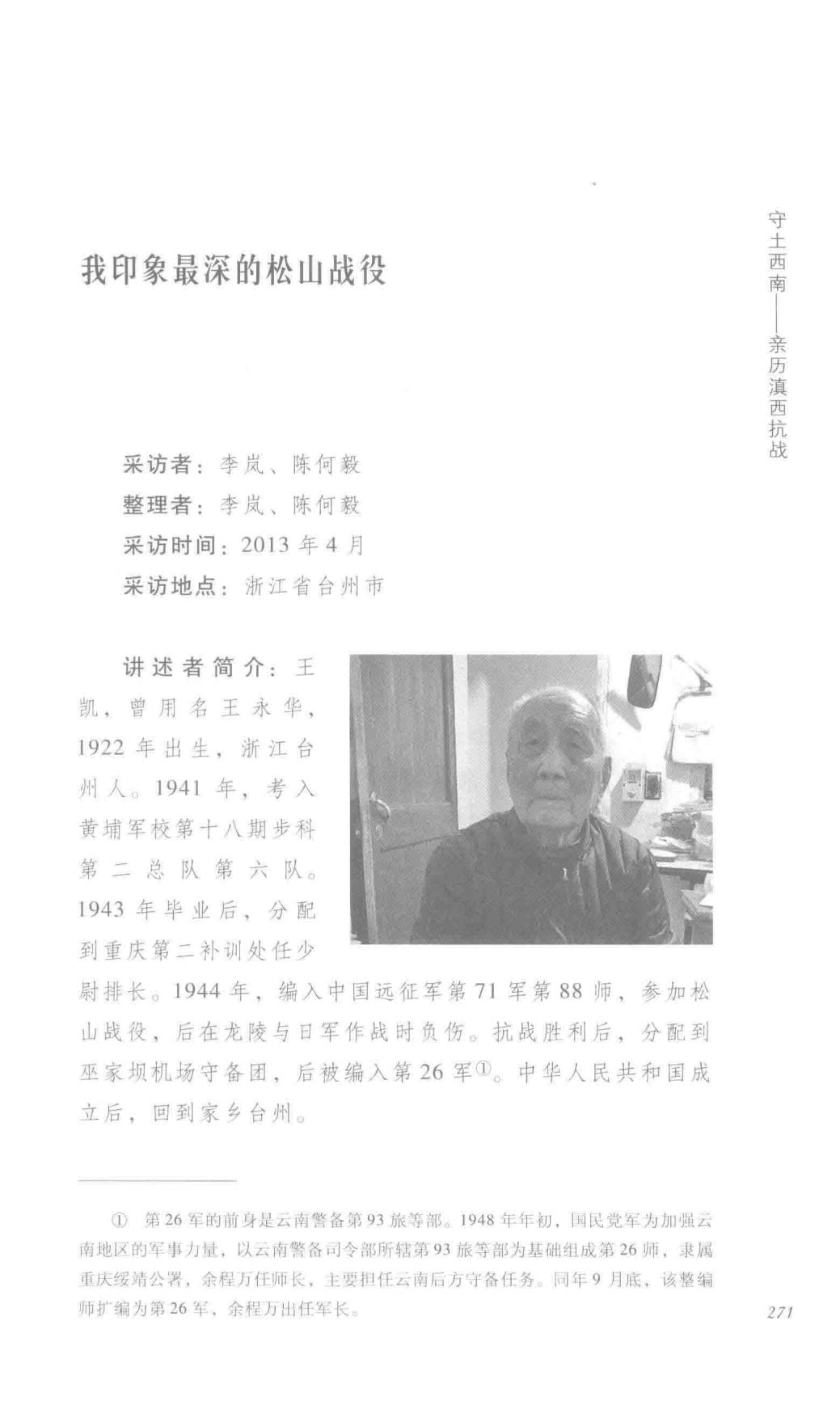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