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革命、救亡被视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三大主题,鲁迅形象被不同的历史主体赋予了启蒙、革命或救亡的意义,生成了“启蒙鲁迅”、“革命鲁迅”与“救亡鲁迅”的形象系列。相较于“启蒙鲁迅”与“革命鲁迅”在不同历史阶段被反复言说,“救亡鲁迅”主要建构于1936—1945年的战时语境。《救亡情报》1936年5月30日发表的《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初步涉及“救亡鲁迅”的形象塑造,鲁迅逝世后由“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印制并散发的《鲁迅先生生前的救亡主张》正式开始“救亡鲁迅”形象认定,之后全国文艺界的一系列悼念活动,将这一形象的建构推向高潮。北平的高校与左翼文学团体众多且处于“国防前线”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救亡鲁迅”的形象建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北平左翼文学社团及高校学生团体发起的纪念活动,既彰显了鲁迅在北平左翼文化界尤其是广大青年中的重要影响,同时也以一种“入人深”“化人速”的形式实现了对“救亡鲁迅”的形象建构。但这些活动及其彰显的价值立场迄今尚未得到系统的梳理。[1]本文以北平左翼文艺社团期刊为考察对象并兼及《世界日报》《北平新报》《华北日报》等大众媒体,对鲁迅逝世后北平左翼文艺界的悼念活动进行梳理,在呈现北平左翼文艺界对鲁迅形象的特殊体认的同时,揭示“救亡鲁迅”形象建构的内在肌理及其历史意义。

宋庆龄、茅盾、巴金、胡风等人为鲁迅抬棺

鲁迅丧仪队伍
一
北平各界(包括各文艺团体及各大学学生组织)曾发起筹备全市规模的追悼会,1936年10月25日的《华北日报》第九版登载消息称“鲁迅追悼会现正进行联络工作中参加者已有十余团体”[2];10月31日的《世界日报》称“平市扩大追悼鲁迅仍在筹备……鲁迅追悼会之筹备,未曾稍懈,联络工作,仍甚积极……由文艺界名流署名发起筹备,请各文艺团体,及各校学生代表各文化团体等广为参加……已决定无论如何于下周内开成追悼会,因此事颇具时间性也”[3]。据李何林11月4日写给孔另境的信“以后如有大规模的全市联合追悼会,当可供给点材料,只怕难以实现耳。因为到现在尚无具体办法”[4]。筹备良久而未能举行,据《庸报》载系“因时局关系、不能举行规模较大之集合、故筹备事、暂行停顿,俟经向各方接洽后、再进行整顿”[5],内在和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京派文人、左翼作家及各界代表等筹备人的“鲁迅观”存在较大分歧。
全市范围的大型追悼会虽未能举行,北平高校和各文艺社团以追悼会、纪念会、座谈会等形式举办的分散的追悼活动却相当活跃。据不完全统计,1936年10月先后召开追悼会的北平高校和文学社团有中法大学(10月23日)、清华文学会(10月24日)、民国学院(10月26日)、北京大学文艺研究会(10月29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0月30日)等,除北京大学文艺研究会组织的追悼会及演讲人无明确的左翼背景外,其余追悼会基本都由左翼社团组织发起或约请左翼人士进行演讲。
10月24日下午在清华大学同方部召开、由清华文学会发起,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和救国会等团体参加的追悼会具有代表性且影响广泛,《世界日报》《北平新报》《清华副刊》等报刊均有报道,并有相关文字收入1937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追悼会入口陈列鲁迅著作和遗像、遗墨,清华文学会编印的《追悼鲁迅专刊》(含鲁迅著作目录、鲁迅当年发表在《语丝》的自传以及清华学生写的献辞),会场内陈设清华文学会的挽联、学生自治会与救国会的花圈。追悼会最后朱自清、闻一多和李长之分别发表讲话。[6]
中法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追悼会也值得关注。中法大学追悼会的演讲人是曹靖华和李何林,曹靖华在讲演中哀悼“鲁迅死得太早”,他的死“失掉了我们的灯塔”,李何林对“转变说”提出了批驳,认为鲁迅“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转变!就是由生到死”[7];民国学院追悼会的演讲人是齐燕铭与孙席珍。齐燕铭在演讲中对章太炎与鲁迅进行比较,认为“鲁迅先生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争取民族的自由”上与章太炎是一致的;但“在程度上”,“章先生的晚年好似一位解甲归田的宿将。而鲁迅先生直到死的那天还是全副武装在火线上,努力应战的一员先锋”,所以“鲁迅先生的死比起章先生的死对于今日民族革命运动上,其损失更为巨大”[8];孙席珍以“鲁迅先生在文坛上的斗争”为题,对梁实秋的鲁迅“转变论”及周作人的“悲观说”进行了驳斥,指出纪念鲁迅“必须继承他的意志,接受他的指示,学习他的经验,千百倍的加强我们的努力,尤其是他临终前所用力促成的,为民族求生存的联合战线,我们必须竭力使之实行”[9]。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追悼会采取座谈形式,孙席珍、李何林、李辉英等人出席。孙席珍认为“鲁迅始终为一现实主义者”“始终把握现实,而无所谓‘转变’”“有人谓鲁迅为消极的悲观者,观察未免歪曲”,李何林也指出“鲁迅之思想为封建社会制度所造成……为三十年来整个文化思想之反映”,“鲁迅逝世与救亡运动,及青年今后之任务”等议题是座谈中最受关注的话题,“引起强烈之兴趣与辩论,结论是纪念鲁迅必须促成统一战线于文学界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之建立”。[10]追悼会的主题除了驳斥梁实秋、周作人等人提出的“转变说”和“悲观说”之外,主要聚焦在鲁迅与民族救亡及文学界统一战线问题上,这既是1936年的特殊时局以及北平作为“国防前线”的地理位置使然,同时也是左翼文化界响应统一战线政策的必然反应。
二
除追悼会外,各社团出版的专刊、专辑(专叶)和专书是左翼文化界鲁迅悼念活动中最为重要的部分。1936年底和1937年初出版的北平左翼文学社团期刊,都以显著篇幅登载了追怀鲁迅的文章。以十二九文艺社成员为主要力量的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以唐诃为中心的文地社出版的“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和“纪念鲁迅先生木刻特辑”以及《清华周刊》《清华副刊》第45卷第1期设置的悼念鲁迅的专栏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几种。

《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1936年版
《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1936年11月上旬出版,系鲁迅逝世后最早出版的一本纪念专集。纪念集以鲁迅头像为封面,扉页插图为鲁迅手握如椽巨笔,之后是《挽歌三首》(《鲁迅先生挽歌》《安息歌》《哀悼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张》《鲁迅先生遗作选》(包括《自嘲》《八月的乡村·序言》)等文章;其后是“LU HSUN: AN APPRECIATION”(《对鲁迅的景仰》)、《挽诗》《他去了,可诅咒的时代还没有击退呢》、《怀念鲁迅先生》、“A FOREIGNER’S TRIBUTE TO CHINA’S ‘VOLTAIRE’”(《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等论文及纪念文章;再后是专栏“音容宛在”(收《鲁迅买书》《出殡的行列》《瞻仰遗容》);其后是《鲁迅底死》《秋风里底颤抖——纪念文化巨匠鲁迅》《追悼鲁迅先生》《鲁迅死后怎样》等悼文,最后是赵荣声撰写的《后记》及《附录:鲁迅先生译著一览表》。从栏目设置与文章编排看,不乏匆促编就的痕迹,但内容相当全面,从整体上建构起较为丰富立体的鲁迅形象。这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对鲁迅的景仰》(谢迪克著,龙门等译)、《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施乐著,蕊译)。
在《对鲁迅的景仰》中,英国评论家谢迪克将鲁迅定位为“战斗员、人类的爱护者、诗人、中国的革命英雄”并认为“在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文学实验之中,其他中国文人的功绩也许还有各种争议和不同的看法,只有鲁迅的贡献和价值是被众人所肯定的”。文章通过对《阿Q正传》《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等代表作的分析,总结出鲁迅作品的三大特质——“悲愤的诚恳”和因此产生的“透彻的人生批评”、“仁慈”和“对同胞的同情”、“对故乡的眷恋”。[11]《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的作者“施乐”即《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她将鲁迅称为“刚强勇敢的革命志士”,是“几个仅有的”“在民族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的伟大的作家”,鲁迅“激发中国大众的情绪来反抗一切精神物质上”的“痛苦”。海伦·斯诺的鲁迅论揭示鲁迅战斗的知识分子的特点。《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提供了两位英美学者对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的判断与认知。

《文地》1936年第1卷第1期
1936年11月和12月出版的两期《文地》是纪念鲁迅的重要载体。创刊号封面主要版面由“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八个大字和鲁迅遗容照片组成,在扉页、封底等显著位置登载鲁迅先生遗像、手迹并在第二页以特殊字体刊载鲁迅遗作《〈全国木刻联展专辑〉序》,还刊发了《对鲁迅先生的献祭》(相当于发刊词)、《哀鲁迅先生》(唐诃)、《我敬爱的鲁迅先生》(梁榛)、《文艺的驱敌政策》(黄既)等文章。第二期辟有“纪念鲁迅先生木刻特辑”,扉页刊载曹白的木刻《鲁迅〈祝福〉插图》,目录后的第1、2页还刊载了惟元、李桦二人分别绘制的木刻《鲁迅先生像》及新波的木刻作品《鲁迅先生遗容》。黄既的《文艺的驱敌政策》除旗帜鲜明地支持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外,提出的“认敌做友是莫大的错误,应该马上起来反对;化友为敌也是莫大的错误,也应该马上起来改正”[12],与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表露的对“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的疑虑不谋而合。
1936年11月出版的《清华周刊》和《清华副刊》均设置悼念鲁迅的专栏。《清华周刊》除刊载《鲁迅先生遗像及签名》外,还刊载了主编王瑶的长文《悼鲁迅先生》及以“古顿”笔名发表的杂文《盖棺论定》、文艺栏主任瑛(孔祥瑛)的《挽诗》以及(韦)君宜的《哀鲁迅》、罗白(赵德尊)的《悼鲁迅诗》、李可宗关于《鲁迅杂文集》的书评;《清华副刊》则编发了鲁特(张卓华)的《鲁迅先生》、(李)伟华的《献给伟大的导师》以及赵俪生的《鲁迅追悼会记》三篇文章,撰稿者均为清华左翼社团“清华文学会”的骨干成员。其中,王瑶的《悼鲁迅先生》是最为重要的一篇。王瑶将鲁迅视为“《新青年》时代的诸战士”中“能始终领导着时代而未为时代所遗弃了的,能始终保持着一致的前进步调的”唯一的一位,全面概括了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及作为“一个进步的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努力和成果”。[13]
时代文化社、黎明社等左翼文艺社团杂志也刊发了多篇鲁迅纪念文章。《时代文化》创刊号设置“追悼鲁迅专页”,编发了《战士丧殡速写》《哭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追悼会在旅途上》及该社同人悼文四篇,(齐)燕铭的《念鲁迅先生》中,“鲁迅先生的死,不是幻灭,而是一个震动”“我们纪念鲁迅先生,不是用悲哀的泪,而是用愤怒的火”[14]也是对所有鲁迅悼念活动主旨的概括。《黎明》创刊号设立“追悼鲁迅”专辑,刊载蕴光的《悼鲁迅》、李雷的《悼鲁迅先生》、天佑(丘琴)的《别了,我们中国的高尔基》以及芬君的《鲁迅死了!》四篇悼文;《文学导报》虽然没有开列“悼念鲁迅”专辑,但也发表了余修的《挽诗》、恺夫的《悼鲁迅先生》、金台的《忆鲁迅》三篇悼文,彰显了清晰的左翼立场与战斗风格。承接《时代文化》的《文化动向》杂志、中国诗歌作者协会的《诗歌杂志》、十二九文艺社的《青年作家》、榴火文艺社的《联合文学》等北平左翼文学期刊也都以显著篇幅或在重要位置登载了纪念鲁迅的文章;清华文学会的魏东明、今日文学社的魏伯等人同时也在《实报半月刊》《益世报》《群鸥》等报刊发表悼文,将北平左翼文艺界的声音传达到京外报刊及非左翼阵营。
三
在悲恸与激情中,我们
高呼着口号:
我们民族解放导师永远不死!
我们要踏着鲁迅先生血路前进!我们都睁大着两眼,脸孔燃起来,合跳着一颗巨大的心,我们的大口像溃决河堤似的把声音拼裂起来,我们唱救亡行曲。
汽笛呜咽地在向前突进,车轮在脚底下和着悲壮的悼歌![15]
此段文字出自《铁篷车中追悼鲁迅记》,作者吴山(伍石夫)系北平左翼文艺社团榴火文艺社主要成员。文章记叙他们在开往前线的铁篷车上为鲁迅举行追悼会的情形,对鲁迅的书写被自然置放在了“救亡”的情境中。这也是北平文化界鲁迅悼念活动的一个特色。鲁迅在被赋予“伟大的导师”“文化巨人”“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领袖”“民族解放的斗士”等多重意义的同时,还被特别赋予了重要的“救亡”色彩。
对“救亡鲁迅”的强调,首先见于各大学追悼会的挽联与标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鲁迅座谈会的挽联是“民族正艰危,剧怜睡狮未醒,振聋犹须作呐喊;世途多荆棘,太息哲人竟去,枕戈那许尚彷徨”[16];中法大学追悼会会场入口挂有“纪念鲁迅要从民族解放运动做起”的标语,挽联是“革命导师鲁迅先生千古”“国难方殷正须先生支大厦,良师竟逝怎教我辈作苦撑”[17];清华大学追悼会的挽联是“树新兴文艺之教育,教育青年,教育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战斗,战斗到底,战斗到死”[18];北京大学追悼会的挽联是“东北沦陷一片沃土何日收复,先生逝世伟大先导谁人担当”“为民族解放为劳苦大众拼将生命奠大路,看强敌压境看跳梁小丑誓承遗志争自由”[19]。
其次,强调“救亡鲁迅”是诸多资深左翼文化人士言说的重点。谭丕模的长篇论文《鲁迅作品的时代性——纪念鲁迅先生》,将对鲁迅作品时代性的分析作为纪念鲁迅的“奠仪”。他将鲁迅的奋斗精神界定为“救亡运动”中“发生”的“一种伟大的力量”,并指出“鲁迅先生之死,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文化界的损失,不仅是中国民族解放战线上少了一位战士,而且是全世界弱小者解放战线上少了一位战士”。文章以阶级论视角将鲁迅的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认为鲁迅“以努力发动民族革命战争的斗士资格出现者”[20]的第四阶段写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在鼓吹发动民族革命战争,从战争中去求中国民族的生存”,“他这几年来的杂感,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段,以至于每一篇,都浮动着反帝精神和救亡情绪”,“假使鲁迅还健在的话,他一定又是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柱石,努力于救亡工作及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写作”[21]。谭丕模对鲁迅杂文的理解反映出左翼文化阵营亟待借助鲁迅的影响力扩大救亡宣传力度的紧迫性,“民族魂”的鲁迅也被悄然置换为“民族解放斗士”的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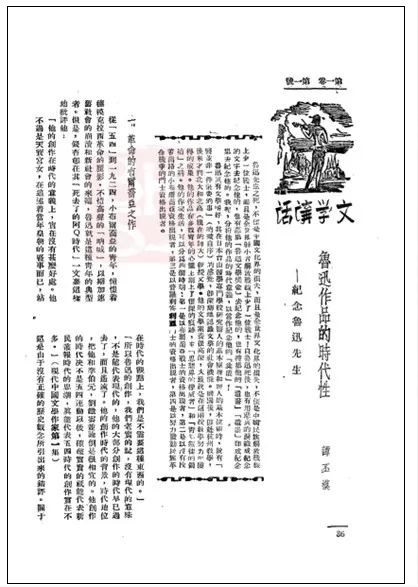
谭丕模:《鲁迅作品的时代性——纪念鲁迅先生》(上),《文化动向》第1卷第1期
曹靖华强调鲁迅对全人类的意义及对抽象的“黑暗”的战斗色彩。曹靖华认为,“救亡”斗争中“身先士卒的宿将”鲁迅与“集体主义者”、“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深切的痛恨中庸主义,痛恨妥协主义”的“坚决的反自由主义者”鲁迅是一致的,鲁迅的死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军中我们阵亡了一位身先士卒的宿将”,使人们“感到救亡工作的艰巨”并“悲痛他在领着千百万大众在坚毅英勇的民族解放的进军中骤然的阵亡”[22]。
最后,“救亡鲁迅”的形象,也是文地社等左翼文学社团凸显的要点。除伍石夫的文章外,《黎明》、《文地》以及《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等书刊同样把为民族争自由的“救亡鲁迅”形象放到了重要的地位。李雷的《悼鲁迅先生》将鲁迅之死与“九一八”之后的民族危机相联系[23],成为北平左翼文学期刊中的主题倾向。比如《文地》“哀悼鲁迅先生特辑”中《对鲁迅先生的献祭》,鲁迅之死与东北民众之死的对比,凸显了鲁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意义;鲁迅之死与高尔基之死的对比,则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困境与时局的艰难。最后,作者号召读者“把做奴隶的期限缩到最短短度”“挣得民族的自由解放”作为对鲁迅的献祭。
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出版的《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扉页印有“我们愿以庄严的民族解放工作来纪念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字样,其后的首篇文章即为《鲁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张》,通过“对于学生救亡运动的主张”“对于联合战线的意见”“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三段文字,将鲁迅定位为“救亡文化运动”中的“伟大的导师,和一个坚强的战斗员”[24]。《鲁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张》系照录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在鲁迅葬仪中印发的文字,三段文字中的前两段录自《几个重要问题》[25],第三段则录自《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的“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三段文字中的前两段是否系鲁迅原意存在一定疑议。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曾就《救亡情报》的采访对其说“你看,记的完全不是我的话,是记者自己的话”,冯也认为“访问记中记的鲁迅先生的话不象鲁迅先生的口吻,大半是一般的道理”[26]。诚如王瑶在《悼鲁迅先生》一文所表达的:“鲁迅先生在病中,在死前,尚屡次不忘而且竭力促进的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和文艺界的联合问题,这是时代课与了这一代人的重要使命,也是鲁迅先生遗留下而必须我们所担负起来的重要工作。完成鲁迅先生的遗志才真正是纪念了鲁迅,也才真正够得上一个纪念鲁迅的人。”[27]这一点,也许正是北平左翼文化阵营试图建构“救亡鲁迅”形象的根本原因——至于“救亡”的具体内涵是否准确符合鲁迅本意,则已不是那么重要。
注释:
[1]李斌《鲁迅逝世后北平文化界的反响》(《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一文对青年学生悼念活动的论述中已对北平左翼文化界有所涉及,但“左翼文化界”及左翼文学社团均未作为独立的文化力量进入考察视野。
[2]《鲁迅追悼会现正进行联络工作中参加者已有十团体》,《华北日报》1936年10月25日。
[3]《平市扩大追悼鲁迅仍在筹备》,《世界日报》1936年10月31日。
[4]《李何林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5]《文化界联合鲁迅追悼会暂停止筹备》,《庸报》1936年11月4日。
[6]俪(赵俪生):《鲁迅追悼会记》,《清华副刊》第45卷第1期,1936年11月2日。
[7]白林:《中法大学鲁迅追悼会记》,《世界日报》1936年10月28日。
[8]齐燕铭:《鲁迅先生在历史上的地位——鲁迅先生追悼会的讲演》,《民国学院院刊》1936年第6期。
[9]孙席珍:《鲁迅先生在文坛上的斗争——鲁迅先生追悼会的讲演》,《民国学院院刊》1936年第6期。
[10]《平大法商学院学生鲁迅座谈会谈述辩论均强烈结论是纪念鲁迅须促成统一战线》,《世界日报》1936年10月31日。
[11]谢迪克:《对鲁迅的景仰》,《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1936年版,第17~21页。
[12]黄既:《文艺的驱敌政策》,《文地》第1卷第1期,1936年11月10日。
[13]王瑶:《悼鲁迅先生》,《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1936年11月1日。
[14]燕铭:《念鲁迅先生》,《时代文化》第1卷第1期,1936年11月17日。
[15]吴山(伍石夫):《铁篷车中追悼鲁迅记》,《联合文学》第1卷第2期,1937年2月1日。
[16]《平大法商学院学生鲁迅座谈会谈述辩论均强烈结论是纪念鲁迅须促成统一战线》,《世界日报》1936年10月31日。
[17]《中法大学鲁迅追悼会记》,《世界日报》1936年10月28日。
[18]俪(赵俪生):《鲁迅追悼会记》,《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1936年11月2日。
[19]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20]谭丕模:《鲁迅作品的时代性——纪念鲁迅先生》(上),《文化动向》第1卷第1期,1937年3月5日。
[21]谭丕模:《鲁迅作品的时代性——纪念鲁迅先生》(下),《文化动向》第1卷第2期,1937年3月20日。
[22]平略(段若青)记:《鲁迅去世后的观感——1936年10月曹联亚在平大女院的讲话》,《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8期。曹联亚为曹靖华原名。
[23]李雷:《悼鲁迅先生》,《黎明》第1期,1936年12月1日。
[24]《鲁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张》,《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1936年版,第6页。
[25]《夜莺》第1卷第4期,1936年6月15日。该文系编者据《救亡情报》1936年5月30日发表的《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一文整理而成。
[26]《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89页。
[27]王瑶:《悼鲁迅先生》,《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1936年11月1日。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