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无论是其涉及地域的广阔度,延续时间的长久度,还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力,及其绵延不绝的现实反响,毫无疑问,都将永垂于中国的史册。但是,在抗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光环笼罩之下,抗战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却姗姗来迟,作为学术研究范畴的抗战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起步,以一九八五年的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为其第一个高潮。从此之后,因为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抗战史研究方成为国内历史学研究中最为热门的专门史(特定时段和特定主题)研究领域之一,以每十年纪念为契机,发表论著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历史主题的研究,而其话题的热度和社会关注度又为其他历史主题所不及,并且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将保持这样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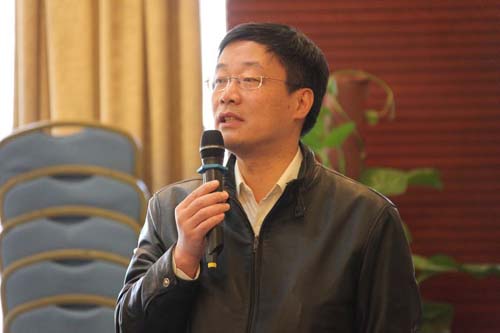
作者汪朝光,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历史研究是向后看的学问,但是,历史研究者是站在当下回望过去的历史,因此,历史研究从来都不缺少“当代性”的意义,抗战史研究更是如此。说到底,研究抗战,通过研究者的“主观”思考反映出的“客观”历史,或可集中在当年我们怎样抗战,以及由此发端的今天我们如何写史。
八十年代以前的抗战史研究,多半建基于“人民战争”的概念,以敌后战场为中心。例如敌后战场的“麻雀战”,以三五成群、出没无常、打了就跑式的零散出击,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于历史事实而言,这确实是当年抗战中的敌后游击战所走过的路。抗日战争的“人民战争”论,是以阶级论为基础,强调抗日战争的革命意义,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而且随之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因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具有一气呵成的连贯性,由中共革命建政的视角观察,其间有机的逻辑联系,一目了然。
以一九八五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发端的抗战史研究大潮的来临,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下,着眼点开始大幅度扩展,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以及与正面战场相关的诸多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诸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国民政府的战时因应、正面战场的历次会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国共合作及全民族抗战的意义、抗战中的国际关系,等等,得到了学界的重新审视,出现了众多研究成果。抗日战争的国家意义—这场战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在战争中得到了什么?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主题,并大体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也得到了辉煌的胜利成果,如中国大国地位的确定,在相当程度上,便是这场战争留给后人的胜利成果,尽管这样的大国地位那时还是有点虚幻。一九九五年,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明确将抗战的意义定位于近代中国的“复兴枢纽”,体现了学界对抗战于中国国家意义的高度评价。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抗战的国家意义论述,并不似抗战的革命意义论述那般简洁明快,能够得到一致的认同(即便是不认同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和海外学者,也认同抗战对于共产党革命的意义)。战时中国,客观上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领导力量,两者既有对外坚持抗战的一致性,又有对内政治斗争的分歧性,更由于战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曾经的执政党国民党失去了大陆政权,因此,抗战的国家意义,便有了相当的争议性。毕竟,国家不是个虚空的概念,国家是由具体的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中活动的人所构成的,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未必都那么一致,因此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也自然有别。例如,当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接受各国对于抗战的援助时,心态是坦然而乐意的,但是当这些援助有可能为了战争的需要给予其政治对手共产党时,其心态又是抗拒而忐忑的。反之亦然。这并不决定于某个个人的喜怒好恶,但如此这般的历史事实反映到抗战史研究中,如何解读便也成了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最直白的说法就是,谁领导了抗战?
“谁领导了抗战”,这样的话题固然有其争议性,但其能够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恰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重大进步,因为在过去的年代,讨论这样具有相当政治敏感性的话题是不可能的。早在抗战史研究刚刚开始起步的一九八八年,著名史学家胡绳先生就曾言简意赅地评论道:“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溃退,等等。”胡绳先生没有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强调要深入研究,尤其要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对于领导权的争夺,“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领导权问题的”。胡绳先生不愧是史学大家,三言两语,要言不烦,便点明了抗战领导权问题争执的关键所在,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就事论事地争执领导权问题,我们又能比胡绳先生当年的提示进步多少呢?
其实,在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前提下,抗战的领导权确实有个“争夺”的过程,而且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因为两党各有其社会基础、政治理念及实践,这些都不因抗战而湮灭于无形,相反,更因抗战提供的同场竞争舞台而凸显出两党“争夺”的必然性。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刚刚爆发不久,国民党内已经有人意识到这样的“争夺”不可避免及共产党影响的快速提升。据时任行政院参事陈克文的日记记载,他感觉:“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其他各党各派却乘这中心势力削弱的时候,大事活跃。许多人仿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甚至有人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则认为:“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可见,国民党内当时即有不少人对国共“争夺”的前景不那么乐观。更不必说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指挥下的军队在全世界同盟国军队一路高歌猛进的氛围中,却在豫湘桂战役遭遇又一次大溃败,从而在其党内外引发巨大的政治震动,以致蒋介石在对高级干部训话时说:“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地位,低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血性,还能够毫无感觉么?还能够因循下去么?”所以,从抗战的全过程观察,国共两党在领导权方面的此降彼升,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与其纠结“谁领导了抗战”,不如踏实地研究抗战领导权转移的过程,或可使我们可以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历史全方位的意义。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史研究,民族战争的视角,得到更多的关注,在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这是非常顺理成章之事。或许,这样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在革命的或国家的视角之外,对于这场战争有更宏大层面的观察,从而克服其过往有些单一性的面相。例如,抗战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意义,已然被学界所关注。日本的入侵,使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国破家亡”,从而自然而然地焕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中国不会亡”的高昂呼声,如同法国《人道报》当年的评论所言:“许多年以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的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矗立了起来。”由此出发,抗战时期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才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对于抗战时期的叛国通敌者,仅仅以传统的“汉奸”论,其实是可以讨论的,与其说他们是“汉奸”,不如说他们是“国奸”。
三十多年来,抗战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其间得益于研究环境的宽松、史料的大规模开放、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广泛而密切以及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努力进取。以研究时段论,出产的论著数量最多(高峰年度著作出版数百种、发文数量数千篇);以研究主题论,涵盖了抗战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过去很少有人关注的论题,如抗战时期的基层社会和民众生活,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以研究结果论,新见迭出,许多学术看法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也为社会各界所接受,如关于正面战场的作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等等,现在的争论较以前已经少了很多。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抗战史研究有待发展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研究空白及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仍然很多,诸如缺乏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综合性、高水准的研究论著,有关战时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综合研究与分类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对于战争中的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的研究仍然不够细致入微,研究者有时仍然易受各种现实的、政治的、外部的因素的干扰(包括新兴网络空间讨论的影响)等等。这些方面都有待抗战史的研究者在未来以扎实可靠的个案研究为基础,以学术为本原,给出客观求实的分析与解读。
如果就宏观而论,未来的抗战史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亟待深入。一是现代化的视角的战争观察。中国的抗战,确实打得非常艰难,甚至于在八年的全面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仍然没能守住一个想守住的大中城市(上海坚守了三个月,衡阳坚守四十七天,长沙四次会战最终仍然失守),与苏军在苏德战场坚守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成功范例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军队在上海以德式装备的最精锐的一个集团军(三个师)的压倒性数量优势主动发起进攻,仍然不能歼灭为数远少于己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其间反映出的,其实是中日两国当时巨大的全方位的现代化水准差异。须知,在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中国全年的钢产量不过数万吨,而日本的产量则几乎百倍于中国,建基于此,中国也无法形成可以抗衡日本装备的本国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像苏德战场那样双方动辄出动数千辆坦克的会战,像太平洋战场那样双方不时出动上百艘军舰的海战,便难以发生在中国战场。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肆虐于后方各大都市上空,今天我们后人痛恨当年日军的残暴,痛惜无数平民无辜丧失的生命,其实那也是中国现代化程度低下而导致的军事能力低下的真切映照。更不必说,现代化是综合性水准的考量,以抗战时期最为后方民众所诟病的被强迫“抓壮丁”式的征兵制为例,也不过是现代化程度低下的某种反映而已。很难想象,一个连正常的人口普查和户籍制度都没能建立的国家,能够建立现代的征兵制度。因此,有关这场战争研究的现代化视角便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对此有透彻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多重面相。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战争观察角度,是国际化的视角。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便不仅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而与远东国际关系及相关各大国的博弈有千丝万缕的纠葛,战争的进程既受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强烈影响,又以自身的力量影响着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卷入战争,蒋介石认为,“抗战政略之成就已达于极点”。然而,美国的参战固然使蒋介石从此不再担心单独对日抗战的种种艰辛,但也使蒋介石在对美关系中因美国的强势而不时处在被动地位,直至发展到美苏协调订立“雅尔塔密约”,严重伤害到中国的主权。如果我们对国际关系和大国博弈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就不能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得失有充分的评判。再者,对于中国在战争中的对手—日本,现有的研究仍然比较欠缺,仅从现有研究中较少引用日文资料的现状,我们便可知在这方面能做的事其实还有很多。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今天我们回望历史,我们对当年怎样抗战知道了多少?又对当下如何写史有何样的感受?可能较之三十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较之理想的状态,仍然有着漫长的距离。美国史学家易劳逸教授曾有言:若不是嗣后的那场内战掩去了抗战胜利的大部分光彩,则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会把它当作一曲最为壮丽的史诗来加以歌颂。那么,作为战争发生地的中国历史学家,便责无旁贷,应该以更为开阔的心态,跳出简单的、功利的、纪念性的战争史叙述范式,以科学的立场,坦诚的研究,恢弘的笔调,写出我们民族这曲“壮丽的史诗”,从而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方不负千百万先人的无私奉献和壮烈牺牲!
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无论是其涉及地域的广阔度,延续时间的长久度,还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力,及其绵延不绝的现实反响,毫无疑问,都将永垂于中国的史册。但是,在抗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光环笼罩之下,抗战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却姗姗来迟,作为学术研究范畴的抗战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起步,以一九八五年的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为其第一个高潮。从此之后,因为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抗战史研究方成为国内历史学研究中最为热门的专门史(特定时段和特定主题)研究领域之一,以每十年纪念为契机,发表论著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历史主题的研究,而其话题的热度和社会关注度又为其他历史主题所不及,并且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将保持这样的地位。
历史研究是向后看的学问,但是,历史研究者是站在当下回望过去的历史,因此,历史研究从来都不缺少“当代性”的意义,抗战史研究更是如此。说到底,研究抗战,通过研究者的“主观”思考反映出的“客观”历史,或可集中在当年我们怎样抗战,以及由此发端的今天我们如何写史。
八十年代以前的抗战史研究,多半建基于“人民战争”的概念,以敌后战场为中心。例如敌后战场的“麻雀战”,以三五成群、出没无常、打了就跑式的零散出击,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于历史事实而言,这确实是当年抗战中的敌后游击战所走过的路。抗日战争的“人民战争”论,是以阶级论为基础,强调抗日战争的革命意义,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而且随之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因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具有一气呵成的连贯性,由中共革命建政的视角观察,其间有机的逻辑联系,一目了然。
以一九八五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发端的抗战史研究大潮的来临,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下,着眼点开始大幅度扩展,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以及与正面战场相关的诸多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诸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国民政府的战时因应、正面战场的历次会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国共合作及全民族抗战的意义、抗战中的国际关系,等等,得到了学界的重新审视,出现了众多研究成果。抗日战争的国家意义—这场战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在战争中得到了什么?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主题,并大体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也得到了辉煌的胜利成果,如中国大国地位的确定,在相当程度上,便是这场战争留给后人的胜利成果,尽管这样的大国地位那时还是有点虚幻。一九九五年,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明确将抗战的意义定位于近代中国的“复兴枢纽”,体现了学界对抗战于中国国家意义的高度评价。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抗战的国家意义论述,并不似抗战的革命意义论述那般简洁明快,能够得到一致的认同(即便是不认同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和海外学者,也认同抗战对于共产党革命的意义)。战时中国,客观上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领导力量,两者既有对外坚持抗战的一致性,又有对内政治斗争的分歧性,更由于战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曾经的执政党国民党失去了大陆政权,因此,抗战的国家意义,便有了相当的争议性。毕竟,国家不是个虚空的概念,国家是由具体的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中活动的人所构成的,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未必都那么一致,因此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也自然有别。例如,当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接受各国对于抗战的援助时,心态是坦然而乐意的,但是当这些援助有可能为了战争的需要给予其政治对手共产党时,其心态又是抗拒而忐忑的。反之亦然。这并不决定于某个个人的喜怒好恶,但如此这般的历史事实反映到抗战史研究中,如何解读便也成了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最直白的说法就是,谁领导了抗战?
“谁领导了抗战”,这样的话题固然有其争议性,但其能够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恰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重大进步,因为在过去的年代,讨论这样具有相当政治敏感性的话题是不可能的。早在抗战史研究刚刚开始起步的一九八八年,著名史学家胡绳先生就曾言简意赅地评论道:“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溃退,等等。”胡绳先生没有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强调要深入研究,尤其要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对于领导权的争夺,“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领导权问题的”。胡绳先生不愧是史学大家,三言两语,要言不烦,便点明了抗战领导权问题争执的关键所在,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就事论事地争执领导权问题,我们又能比胡绳先生当年的提示进步多少呢?
其实,在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前提下,抗战的领导权确实有个“争夺”的过程,而且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因为两党各有其社会基础、政治理念及实践,这些都不因抗战而湮灭于无形,相反,更因抗战提供的同场竞争舞台而凸显出两党“争夺”的必然性。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刚刚爆发不久,国民党内已经有人意识到这样的“争夺”不可避免及共产党影响的快速提升。据时任行政院参事陈克文的日记记载,他感觉:“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其他各党各派却乘这中心势力削弱的时候,大事活跃。许多人仿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甚至有人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则认为:“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可见,国民党内当时即有不少人对国共“争夺”的前景不那么乐观。更不必说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指挥下的军队在全世界同盟国军队一路高歌猛进的氛围中,却在豫湘桂战役遭遇又一次大溃败,从而在其党内外引发巨大的政治震动,以致蒋介石在对高级干部训话时说:“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地位,低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血性,还能够毫无感觉么?还能够因循下去么?”所以,从抗战的全过程观察,国共两党在领导权方面的此降彼升,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与其纠结“谁领导了抗战”,不如踏实地研究抗战领导权转移的过程,或可使我们可以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历史全方位的意义。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史研究,民族战争的视角,得到更多的关注,在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这是非常顺理成章之事。或许,这样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在革命的或国家的视角之外,对于这场战争有更宏大层面的观察,从而克服其过往有些单一性的面相。例如,抗战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意义,已然被学界所关注。日本的入侵,使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国破家亡”,从而自然而然地焕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中国不会亡”的高昂呼声,如同法国《人道报》当年的评论所言:“许多年以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的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矗立了起来。”由此出发,抗战时期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才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对于抗战时期的叛国通敌者,仅仅以传统的“汉奸”论,其实是可以讨论的,与其说他们是“汉奸”,不如说他们是“国奸”。
三十多年来,抗战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其间得益于研究环境的宽松、史料的大规模开放、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广泛而密切以及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努力进取。以研究时段论,出产的论著数量最多(高峰年度著作出版数百种、发文数量数千篇);以研究主题论,涵盖了抗战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过去很少有人关注的论题,如抗战时期的基层社会和民众生活,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以研究结果论,新见迭出,许多学术看法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也为社会各界所接受,如关于正面战场的作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等等,现在的争论较以前已经少了很多。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抗战史研究有待发展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研究空白及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仍然很多,诸如缺乏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综合性、高水准的研究论著,有关战时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综合研究与分类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对于战争中的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的研究仍然不够细致入微,研究者有时仍然易受各种现实的、政治的、外部的因素的干扰(包括新兴网络空间讨论的影响)等等。这些方面都有待抗战史的研究者在未来以扎实可靠的个案研究为基础,以学术为本原,给出客观求实的分析与解读。
如果就宏观而论,未来的抗战史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亟待深入。一是现代化的视角的战争观察。中国的抗战,确实打得非常艰难,甚至于在八年的全面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仍然没能守住一个想守住的大中城市(上海坚守了三个月,衡阳坚守四十七天,长沙四次会战最终仍然失守),与苏军在苏德战场坚守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成功范例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军队在上海以德式装备的最精锐的一个集团军(三个师)的压倒性数量优势主动发起进攻,仍然不能歼灭为数远少于己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其间反映出的,其实是中日两国当时巨大的全方位的现代化水准差异。须知,在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中国全年的钢产量不过数万吨,而日本的产量则几乎百倍于中国,建基于此,中国也无法形成可以抗衡日本装备的本国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像苏德战场那样双方动辄出动数千辆坦克的会战,像太平洋战场那样双方不时出动上百艘军舰的海战,便难以发生在中国战场。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肆虐于后方各大都市上空,今天我们后人痛恨当年日军的残暴,痛惜无数平民无辜丧失的生命,其实那也是中国现代化程度低下而导致的军事能力低下的真切映照。更不必说,现代化是综合性水准的考量,以抗战时期最为后方民众所诟病的被强迫“抓壮丁”式的征兵制为例,也不过是现代化程度低下的某种反映而已。很难想象,一个连正常的人口普查和户籍制度都没能建立的国家,能够建立现代的征兵制度。因此,有关这场战争研究的现代化视角便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对此有透彻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多重面相。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战争观察角度,是国际化的视角。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便不仅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而与远东国际关系及相关各大国的博弈有千丝万缕的纠葛,战争的进程既受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强烈影响,又以自身的力量影响着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卷入战争,蒋介石认为,“抗战政略之成就已达于极点”。然而,美国的参战固然使蒋介石从此不再担心单独对日抗战的种种艰辛,但也使蒋介石在对美关系中因美国的强势而不时处在被动地位,直至发展到美苏协调订立“雅尔塔密约”,严重伤害到中国的主权。如果我们对国际关系和大国博弈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就不能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得失有充分的评判。再者,对于中国在战争中的对手—日本,现有的研究仍然比较欠缺,仅从现有研究中较少引用日文资料的现状,我们便可知在这方面能做的事其实还有很多。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今天我们回望历史,我们对当年怎样抗战知道了多少?又对当下如何写史有何样的感受?可能较之三十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较之理想的状态,仍然有着漫长的距离。美国史学家易劳逸教授曾有言:若不是嗣后的那场内战掩去了抗战胜利的大部分光彩,则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会把它当作一曲最为壮丽的史诗来加以歌颂。那么,作为战争发生地的中国历史学家,便责无旁贷,应该以更为开阔的心态,跳出简单的、功利的、纪念性的战争史叙述范式,以科学的立场,坦诚的研究,恢弘的笔调,写出我们民族这曲“壮丽的史诗”,从而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方不负千百万先人的无私奉献和壮烈牺牲!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