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晏福标,广西玉林人,早年曾在国民革命军桂系军队中服役任职。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参加衡阳保卫战与侵华日军在衡阳外围雨母山作战时阵亡,时任少校营长,年约38岁。
父亲抗日牺牲这一不幸消息,是由他所在部队于同年9月派人转告我母亲的,当时我年仅9岁。记忆中只知道父亲的职务是营长(不清楚他任职部队的具体番号),牺牲的地点是在衡阳雨母山。
2005年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内地大量地出版了有关国民党正面抗日的各类书刊;新闻媒体密集地回顾报道了那一场伟大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各地群众团体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从而也引发了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和知晓我父亲在衡阳抗日殉国的详细情况。
我首先从《常德、长衡会战》(文闻编)一书中,发现了一篇王玉福先生(原国民革命军第46军新编19师营长)所写的‘衡阳外围雨母山之战’的回忆文章,从中搜索到了一些值得参考的线索,又于2005年底在中国黄埔军校网上登出了一幅名为《寻找衡阳外围战中牺牲的先父晏福标》的帖子,寄希望于知情者能够提供有关线索或信息。今年九月下旬,我趁着赴湖南浏阳参加‘潘裕昆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之机会,奔赴长沙、衡阳寻找有关父亲晏福标的史料。
寻找雨母山
2006年9月24日一大早,我和儿女首先驱车前往南岳衡山,参拜雄伟庄严的国民革命军抗日忠烈祠,得知这里就是长衡战役以及整个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的所有将士之总灵位,也就是说这儿就是我失去六十多年的父亲的安葬之地时,我们一行抗日军人遗属虔诚地进行叩拜,以表达对抗日先辈的崇敬及缅怀,这一拜,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第一次面对一个既抽象又实在的父亲灵位跪拜,了确了一个半个多世纪未能付诸实现的心愿。

笔者在衡阳市内岳屏公园山顶的’衡阳抗战纪念城’的排坊前留影
在参观了山上一处抗战时期蒋委员长和夫人宋美龄的寓所后,我们便按预定的计划下山直奔衡阳市去寻找梦回牵引的‘雨母山’。
‘雨母山’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它如今的面貌是什么样?来衡阳之前我一无所知,只能依靠手中刚买来的衡阳市地图辨认,竟然在西南郊区标有‘雨母山乡’这一地名,根据地图上这一标注,初步断定此处就是我要寻找的方位。
初次到埗,道路不熟,为方便到达,不再停车问途人,即决定租出租车带路前往。由市内的岳屏公园出发,大约半小时便到了雨母山乡政府。因周日政府内无人办公,见到几位象是乡干部的年青人在打扑克牌,我即敲门询问,说明来意,迫不及待地问他们这里是否有一座‘雨母山’时,对方即指身后不远处的山峦正是。此刻我可以肯定我要找的‘雨母山’,就在眼前了。我接着问及他们,作为当地人,是否了解1944年7、8月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这山上进行了一场双方都死伤惨重的激战时,他们表情愕然,一头雾水,全然不知,令我失望。仔细想来,这也难怪,衡阳外围雨母山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大小无数的战役中的一场,距今已过六十几年,岁月流逝,往事如烟,昔日战场,今天已变成开发区。君不见,“雨母山开发区”的广告宣传牌已经横挂于村口的牌坊上,现在的年青人又有多少能知道60年前的抗日战争呢?更不用说这场并不太引人瞩目的战役了。
稍后,我们便自行沿山而上,按照路标的指示向‘雨母山’驶去。随着雨母山的轮廓迎面向我缓缓展开,我脑海里充满了那场惨烈战事的画面。六十二年前中国军队为解衡阳之围与日寇在此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杀声共山谷齐鸣,白刃与电光争色,我忠勇将士奋力拼搏,视死如归;我的父亲、年轻的军官晏福标(第46军某部营长)就在眼前这青青山峦之上,战死沙场,壮烈殉国,其尸骨与数以千计的国军阵亡官兵一样被草草掩埋,忠魂长眠于雨母山的丛林岩石之中。

衡阳西南郊区雨母山轮廓远眺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山腰处,见一寺庙,我们停车入内。寺内非常安静,也看不见香客踪影,但见到几位年长的师傅,当我趋前打听有关当年雨母山战斗情况时,师傅们显得颇有了解。一位师傅告诉我,据他的前辈讲述,那年这后山上的确打过打仗,中国军队整排、整连的士兵战死在山上,无人替他们掩埋尸体。今年三月他上山顶时,还见到有残存的战壕。见我有上山看看的意愿,他好心告诉我说那儿无路可辩,杂草丛生,攀登困难。此时天色已晚,他建议我择日再来,并愿意领路前往。我再次面对雨母山叩拜一轮,权当是亲临了父亲殉难之地,与他的长缅之地有了接触,对他在天之灵有了总算有了告慰。
眼前这座雨母山虽不属名山,却是山高林密,颇有气势。衡阳保卫战时,它是衡阳西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1944年夏秋间,国民革命军第10军被日军围困于衡阳城中,蒋委员长电令第62军由粤入湘,第46军自桂赴衡,增援解围。国军在雨母山一带受到日军的阻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死伤众多。
第46军新编19师战斗详报对于1944年8月5日雨母山之战斗有如下记述:
“5日师仍继续攻击雨母山之敌,由拂晓至午战斗激烈,然我官兵用命,下午4时左右我奋勇冲杀,卒将盘据雨母山之敌悉数歼灭,雨母山遂为我右翼第一线所占领。然时已薄暮,且黑云密布,风雨交加,敌由七里山及东阳铺方面向我两翼包围逆袭,我立足未定,伤亡惨重……”。
今日不枉此行,让我终于找到了雨母山,除了亲自拜祭先父殉国之战场外,并祈愿苍天神明保祐为抗击日寇而牺牲在此长眠的所有将士英灵。
重要的发现
我童年时,曾在家中看到过一本像册,印象中里面的像片个个是军人,佩有皮带,斜挎武装带,头戴大沿帽。因为战乱,像册早已丢失。近年,由于我要四处寻找有关父亲生前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的史料,这个对于军人照片模糊的记忆引起了我的回忆。根据猜测以及从其他黄埔军校通讯录所获得的知识,那本像册很可能是父亲参加军事学校训练后同学们毕业合影留念及同学录之类的东西。那么父亲生前曾参加过什么性质的军训或军校?何年何月在何地受训?这一切都没有留下任实物及记载。父亲会不会是黄埔军校的学员呢?因无证明材料,未敢断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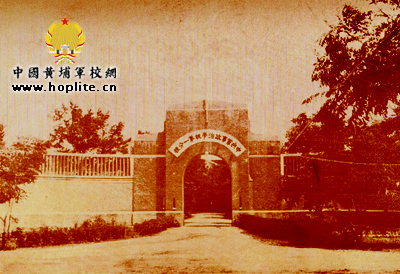
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外貌
今年九月中旬,我曾致电长沙湖南省档案馆请求协助查寻是否存有有关父亲晏福标在衡阳雨母山战役牺牲的记录,诸如阵亡将士名单之类的存档。档案馆工作人员十分热情,答应帮助查找。事隔一天便有了回复。馆方告诉我:找到了一份有关晏福标的历史资料,该资料写有:晏福标,广西玉林人,31岁,民国二十五年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六、七期学员。又说:详细资料需要我本人亲自前往查阅。得知湖南省档案馆给我传递的这一信息以及他们的发现,令我非常激动。
9月26日一大早,我赶到长沙市的湖南省档案馆,因事先预约,因此顺利办妥手续入馆,馆方很快就调出一份档案并附上一张档案卡。我首先浏览这卡片,但见印有姓名、籍贯、年龄、何时何地参加何种反动组织任何职务等栏目。我父亲晏福标的名字就被填写在这张卡片上。卡上显示的内容与我来之前馆方电话告知我的完全一样,只是来之前对于“晏福标民国二十五年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六、七期学员”其中这个“任”字不得其解。既然是学员,为何冠以“任”字?一般理解,在某职务之前加“任”字,但从未见过在“学员”二字前还要加“任”字。再仔细品味这张带有编号的档案卡,才逐渐明白其中的逻辑。因为“晏福标民国二十五年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六、七期学员”这段字是被填写在《何时何地参加何种反动组织任何职务》这一栏中,按照解放后当时的国内政策,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说黄埔军校,是被列为反动组织的,而学员就理所当然地应被列入“任”反动职务了。查到了父亲的史料心喜若狂,激动不已。唯有对馆方仍将黄埔军校的毕业学员,无论青红皂白,是否为抗日捐躯者,都列在反动组织内并“任”职务这样陈旧的做法,心存一丝不快。

父亲晏福标的中央军校毕业照
接着,我查阅了那本案卷(全宗号130,案卷号524)-《中央陆军军事学校第一分校六、七期同学录》,这是六、七两期毕业生学员留影的合订本。同学录中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的校址(于广西南宁)、校旗、校训、校歌及广西军政要人李宗仁、白崇禧的题词。接下来的惊喜是我在第七期步兵科一栏中看见了我父亲一张放大的半身像,像片正上方写有:晏福标 三个字,字迹清楚,照片清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见父亲70年前留下的照片,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语,翻动的思绪九不能平。
我的猜测没有错,父亲正是黄埔军校的学员!这是我一年多来四处查寻的重大收获,更是破解了埋藏在我心中六十年的父亲身世之谜。终于能有机会让我的后代一睹他们从未见过的祖父的容貌了!这对他们是一个清晰的历史交代,我感到如获释重,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感,我的父亲是黄埔人!
初步的分析
9月24日第一次去衡阳西南郊寻找到雨母山抗战遗址,唤起我再赴衡阳档案馆挖掘出是否有衡阳保卫战之雨母山战役的文字记载、特别是父亲所在部队的具体番号及阵亡日期的冲动。于是我于10月16日再次来到衡阳,满怀希望进入衡阳市档案馆,因事先有约,故馆方人员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衡阳抗战铸名城》一书让我阅读,并告知我可供参考查阅的资料全都在这书中,已无其它史料可查了。
该书由政协衡阳市委于2005年9月编印,书内收集了大量的衡阳保卫战史料,不少篇章是由当时亲历者回忆撰写的。令我失望的是,我需要的、想知道的有关雨母山战斗的回忆录可供参考的仅有一篇,且该文我早前已阅读过。不过该书其中的《陆军新编第19师1944年7-9月份阵中日记》、《陆军第46军长衡会战衡阳二塘附近战役战斗详报》,详尽记载了该部队在衡阳外围雨母山一带战斗经过,这对我分析父亲作战部队的具体番号及他牺牲的日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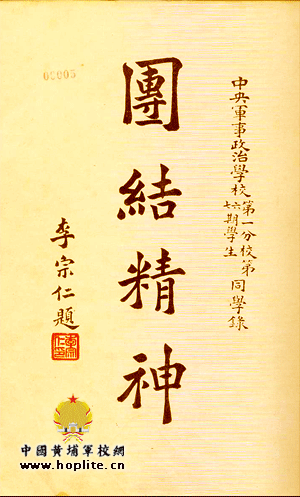
李宗仁题词
据所掌握的史料显示,第46军(军长黎行恕)属桂系军队,下辖新编第19师及175师两个师。当年从广西桂林开赴衡阳参战的部队只有第46军一个军;我父亲的部队在去衡阳作战之前,曾在桂林、兴安一带驻守过(我记忆中儿时曾随母亲由居住地广西鹿寨前往桂林附近探望父亲,还曾在父亲租的民房中住过,这一点可以说明父亲至少不是一名普通士兵,还有,黎行恕的名字在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的教官中出现,而父亲应该是他的学生,在他所率的桂系第46军中任下级军官的可能性极大),以此为根据分析,父亲所服役的部队应该属于第46军。
新编第19师战斗详报记载:“该师奉命于7月25日由桂林用火车输送至黎家坪(湘桂线湖南祁阳以北一个站),26日下午先头部队陆续到达,27日至30日在白鹤铺、鸡笼街(衡阳外围以西南湘桂线上的两个站)一带与日军发生战斗,8月3日至8月9日在雨母山附近与敌激战,白刃肉博、反复冲杀,伤亡惨重”。新编第19师阵中日记记述:“是日(6日)天明后,新19师继55团及56团各一营对雨母山攻击,经我猛烈突击肉博后,于是日午须再攻克雨母山。旋敌仍一度再增援,对我逆袭,数度争夺肉博,前仆后继,不顾一切牺牲与敌冲杀,终以敌据守改设坚固阵地,未能完全毁灭。敌增援逆袭猛烈,我伤亡重大,雨母山又得而复失”。

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旗与校徽
我从第46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及175师由桂林至黎家坪铁道输送计划表中看到,175师三个步兵团最先由桂林南站火车起运的524团,是在8月5日早上6时出发,最后起运的525团第2、第3营是在8月5日20时,也就是说,雨母山战斗最激烈的时候(8月3日-8月6日),第175师并不在该处。据次分析判断,我父亲是在雨母山战斗牺牲的,他所指挥的步兵营属于新编第19师的可能性最大,他阵亡的日期大致确定在8月3日至8月9日间。8月8日守城国军方先觉投降,衡阳失陷,8月10日新编第19师调整部署对雨母山之敌严为戒备,无激烈战斗,不久桂系军队第46军撤回广西。
自去年在中国黄埔军校网上登出寻父晏福标一帖以来,我的许多精力集中在编写岳父潘裕昆的传记上,除得到中国黄埔军校网站长王坚的查寻各地档案馆、黄埔同学会的指引外,并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其间也收到一位邓姓广西朋友寻找在同一时间同一部队失去的祖父的信件。

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训与校歌
自这次研究探索,值得欣慰的是,确定了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基本锁定了父亲生前所属部队的番号(仍需确证)。月底再赴台湾,祈望能够查到衡阳抗战阵亡将士名单,有了我以上的缩小的范围,可能会找寻到实质的历史记录,那就令我心满意足了。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