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组建文工会和第三厅
1935年初,由于叛徒出卖,阳翰笙等第一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被逮捕。3月18日夜,阳翰笙与田汉同僚同铐被押送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囚禁。阳、田被捕后,上海地下党努力设法营救。国民党迫害著名文化人的倒行逆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指责。柳亚子、蔡元培、邵力子等社会名流愿意出面为阳保释。国民党迫于外界的压力和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将阳翰笙由囚禁改为软禁南京,家属被接来作为人质。
阳翰笙在两年半的软禁逆境中,虽在暗探、特务的包围和监视下,但始终坚定、机智地用自己的笔进行战斗。他与地下党取得了秘密联系,在南京唯一民营的《新民报》上,以别人的名义出面开辟副刊《新园地》。用各种化名一连发表了《养狗篇》《打狗篇》《辩奸论》等40多篇投枪匕首式杂文,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和各色投降主义分子。他在《编后》里号召大家都来参加“打狗”,由此在《新园地》上掀起了一场著名的“打狗运动”。
阳翰笙仍然继续创作电影剧本,呼吁抗日救亡。《生死同心》《夜奔》经上海进步影人拍摄放映,引起社会轰动。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和签订对日投降的“何梅协定”,阳翰笙又以话剧为武器,创作了痛斥汉奸的话剧《前夜》和鼓舞抗日锄奸的话剧《李秀成之死》(剧本于1938年1月正式出版)。“七·七事变”国共合作,国民党被迫宣布释放政治犯,阳翰笙才获得自由。阳翰笙这段历史,党组织当时就进行了审查,当即就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
阳翰笙获得自由后,奉党之命到武汉报到。经中共长江局审查,立即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周恩来亲自和他谈话,安排给他两项重要任务——组建文艺界抗敌协会和组建第三厅。
周恩来给阳翰笙的第一项任务,是将全国文学艺术界的抗日力量组织起来。根据中共中央1937年7月15日的指示:“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有着多年左翼文化运动组织经验的阳翰笙,深知党中央此项政策之重大历史意义。过去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十年中,是我党和国民党你死我活的斗争,而现在面临的是要团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救亡力量。他同时也很清楚,这统一战线的团结必然是有斗争的,是一个又团结又斗争的文化联合阵线。
阳翰笙因势利导、力争主动,不失时机地与冯乃超一起在很短时间内,以左翼文化力量为基础,广泛地团结了文化界各方面人士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并和相继成立的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抗敌协会等,联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在八年抗战中,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这些协会始终由进步力量掌握,在全国发挥了团结抗日力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并推进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积极作用。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为保护和营救革命文艺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
周恩来安排给阳翰笙的另一项更复杂的任务,是协助郭沫若筹组第三厅。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一点国共合作的姿态: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由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管下属第三厅(宣传厅),邀请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蒋的意图很明显:利用周、郭的威望,延揽文化界诸多著名人士,既装点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然后,他在将周、郭架空,将第三厅控制在自己手中,继续贯彻他的“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方针。
对我党来说,第三厅是我党在国民政府中唯一可以争取到的合法权力机构。利用它可以突破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突破国民党不许发动群众抗日的“片面抗战”政策,而在国统区广泛宣传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动群众进行“全面抗战”。所以,我党积极争取将第三厅组建成由我党领导的抗日名族统一战线机构。
政治部其他各厅各处都是蒋介石的人。国共两党在政府机构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便集中在第三厅的组建工作上。阳翰笙奉命参加长江局有关建立第三厅的各次会议、讨论策略,与郭沫若一起参加一系列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谈判。
为此,阳翰笙进行了大量艰难、细致的具体工作。他依靠原左翼文化运动的骨干,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以及“东北救亡总会”的力量,将各方面的爱国进步人士团结在我党周围,出色地完成了第三厅的组建任务。
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第三厅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绝对秘密的,周恩来、郭沫若、杜国洋、冯乃超、田汉、董培倩成立特别党小组,周恩来任组长。第三厅还成立了特别党支部,支部书记冯乃超,组织委员刘继平,宣传委员张光年。党支部与党小组之间不发生联系,全体党员单线联系。
文艺界抗日战线核心堡垒
第三厅人才济济,几乎集中了社科理论、文艺理论、评论、戏剧、美术、音乐等各个领域的精英。田汉领导的艺术处,不仅有著名的洪深、冼星海、张曙、石凌鹤、史东山、应云卫、郑君里、程步高、马彦祥、丰子恺、叶浅予、力群、黄普苏、冯法祀、力扬、袁牧之等,也有后来一鸣惊人的傅抱石、李可染、罗功柳等。
自第三厅成立至抗议蒋介石迫令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而集体辞职的两年半内,全体进步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刁难和破坏,进行了大量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推动全民抗战的工作。
阳翰笙作为主任秘书,从事组织工作,任务繁重。他一方面机智的和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十分珍爱每位满腔爱国热枕的同志。他知人善任,善于团结大家(包括第三厅以外的文艺人士),使人人各尽其才。不辞艰辛,与大家共同奋斗创造了抗战初期文艺运动的崭新局面。
第三厅时期的工作归结为十大重大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组织最繁杂、斗争也最尖锐的几项活动,都是周恩来指示阳翰笙亲自负责、策划安排。
第三厅成立,就针对国民党压制群众抗日的片面抗敌政策,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扩大宣传周”和“七·七献金运动”。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合作下,组织了武汉各界声势浩大的持续不断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第三厅人员奔向街头巷尾及各个大小演出场所,以各种生动的、大众化民族化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唤起每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周恩来指示)。全民沸腾,参加游行的人达六十多万,群众的爱国热枕和抗战意识空前高涨。
献金的不仅有达官贵人、资本家、更有广大市民、工人、农民、店员、小贩、人力车夫、甚至乞丐,现金和金银器物总共超过100万元!为监督管理慰问金的使用和分配,由阳翰笙负责,专门组织成立了“慰劳总会”。郭沫若厅长派阳翰笙亲自带队到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并购买了10辆英国道奇牌卡车将慰问品送至10个战区,给八路军、新四军也都送了。为此,叶剑英特地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同志来第三厅致谢。
阳翰笙同时还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为党中央买了两台发报机;另一件是将第三厅人员编辑的大型摄影画册一一日军侵华罪证《日寇暴行录》带到香港印刷。
周恩来利用第三厅政权机构,策划了两项战略性举措。一是在全国几个战区星罗棋布的建立“战地文化服务站”,将第三厅编印的大量文字和美术的抗日宣传品输送至前线,送到国民党的军队去,散发到广大的中、小县城里去,影响很大。
同时,“战地文化服务站”又是在董必武和湖南省委领导下秘密部署豫鄂敌后游击战的筹建据点,这在当时是绝密的。后来,新四军豫鄂游击队迅猛发展起来和这一重要部署密切有关。
二是建立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进入各个战区的国民党军队里。周恩来给各宣传队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是:“随军行动,深入宣传,坚持原则立场,开展统战工作;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各个演剧队在敌人的心脏里机智顽强地开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了我党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在演剧队成立的11年间,周恩来从未间断过对演剧队的领导。每逢重大政治形势变化,他总是派人或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指导演剧队应付各种复杂局面。演剧队不但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历史使命,而且锻炼成为一支在政治上坚强、在艺术上有创新的革命文艺队伍,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阳翰笙还利用第三厅获得军委会政治部的证明信,使文艺界许多爱国志士、团体得以奔赴前线进行摄影、采访、写生作画、宣传慰问。
在战火中诞生,从上海徒步跋涉,一路宣传抗日至武汉的“孩子剧团”,经周恩来亲自向国民党力争归属第三厅后,由阳翰笙负责安排他们的生活、学习和社会活动。他请第三厅的名家给他们教各种文化课,指导他们的活动。“孩子剧团”在党的关怀培育下成长为一支十分活跃的、赫赫有名的、宣传抗日的生力军。
在汉口,国民党军委正在筹建一个摄影场(即后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但是只有空架子,没有电影人才。厂长郑用之知道阳翰笙在上海电影界的影响,特请他支持推荐上海人到汉口参加“中制”。与此同时,史东山、孙瑜等人也找阳翰笙商量,是否可以参加“中制”?
阳翰笙说:“为了团结抗日,可以和他们合作。但是你们要向他们声明,我们是自由职业者,不参加组织,不要高待遇,不要军衔,以避免发生什么事而受军事处分。我们要想办法不被国民党套住。不过,最后决定等到了汉口在说。”
阳翰笙将此事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说:“应该进去,进去是为了占领他的阵地。”于是,阳翰笙组织了一批人进“中制”,他自己被聘为中制的编导委员会主任,主管制片核心工作。特别是在中制归属“第三厅”后,阳翰笙将大批进步影人安排进“中制”,还安排了钱友章等同志在“中制”从事剪接工作。
这样,进步力量在“中制”形成绝对优势。在阳翰笙领导的三年内,“中制”拍摄了11部抗战故事影片(其中四部是阳翰笙编剧),50多部新闻记录片、卡通片。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和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曾在美、非、缅、法、瑞士等国的反侵略大会上放映,反响热烈。罗静予、钱悠璋等编辑的若干集《抗战特辑》,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有的素材被美国个影片公司至今仍在采用。
许多外国观众看完后,自动捐款支援中国抗战。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中制”改组,阳翰笙退出“中制”,但仍安排不少进步影人留在“中制”。此后,“中制”基本上再没有生产新的影片。此时阳翰笙的领导工作已经转移到话剧战线,进步影人们也积极参加到话剧运动中去。
“三厅”还组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壮举。集中在武汉的广大地方戏曲人员受到“三厅”的重视,经过组织学习,爱国热情高涨,他们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希望地方戏剧团体在大后方把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负担起来。这是全面抗战的需要,也是我们对民族、对子孙应尽的责任。”他们第一次深切感到在人格上在政治上得到了尊重。他们激昂的提出“决不给敌人演戏!”的口号,决心统统撤离即将失守的武汉。
上千名地方戏曲人员开始了跋涉千里的大转移。阳翰笙和田汉领导的艺术处,利用政治部第三厅的权利,将所有的民间戏团建成流动宣传队,签发番号和军用护照,并补助路费,使他们全部撤离到内地。他们一路徒步宣传演出,在大后方苦苦坚持到抗战胜利才复原回到原地。所以,中国戏曲界成为日后新中国的一支文化中坚力量是有历史根由的。
“三厅”集中了一批原左翼文化人,外语顶尖人才叶君健、叶籁士等,特别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和廖体仁、郭劳为等日语专家。他们在杜国洋、冯乃超的领导下不但做了大量的对日对外文字、广播宣传工作,而且还接待和安排受到国民党阻挠的外国朋友。
“翰笙同志那时几乎每天要同蒋方党政军有关当局办交涉,磨嘴皮子,进行不卑不亢的斗争。一些我们急得脖子脸鲜红的事,经过翰笙同志的指点和奔走终得到解决。第三厅同事献出了全部力量,而翰笙同志是操劳最多的一个。”(张光年《六十年忠诚服务》)
党领导的第三厅,虽然处在国民政府的夹缝里,但是它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它利用这一点点政权,充分发动群众,将文化战线上的抗日救亡和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到各战区前线和国统区的大后方,成为国统区领导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堡垒。
与国民党有理有利有节斗争
1939年,蒋介石在日寇的政治诱降下,由“片面抗战”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推行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蒋介石反动派对第三厅从来就不断进行限制、刁难、破坏,现在更变本加厉进行迫害。他们强令取缔了“战地文化服务站”,夺走了“三厅”所属“慰劳总会”、“寒衣会”。“三厅”人员和演剧队成员不断遭受逮捕、监禁、暗害,仅演剧队前后就牺牲了数十人。
甚至国民党自己军队的一个“忠诚话剧团”,抱着爱国热枕,1939年底在重庆请马彦祥导演,演出了阳翰笙的激励抗日斗志的话剧《李秀成之死》,反动派竟以“通共匪”的莫须有罪名,丧心病狂地将扮演李秀成的演员李英活埋,将参加演出的二十余名爱国青年枪毙!还牵连了二百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綦江惨案”。
1940年8月蒋介石竟亲下手谕,第三次迫令“三厅”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郭沫若、阳翰笙带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愤而集体辞职,以示抗议。他们宁愿受事业和政治迫害的威胁,也决不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大家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去延安。蒋介石为了防止这批文化人去延安,就提出设立非政权性质的学术研究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直属政治部。
这显然又是蒋介石的羁縻政策。所谓搞研究,不过是将这批文化人圈起来“画地为牢”,手无政权,翻不起三尺浪!我党决定不放弃这一合法的斗争阵地。周恩来做思想工作说服大家:“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可以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他划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以学术、文艺多种活动方式进行斗争嘛!”
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受命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1940年10月1日“文工会”正式成立,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阳翰笙以其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和斗争艺术,襄助郭沫若采取新的策略与方式,开始了更加复杂的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文工会”吸收了比三厅更广泛的进步文化人士。“文工会”一方面集中了一批以郭沫若为首的翦伯赞、蔡仪等杰出的专家学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著书立说,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理论方面都硕果累累。郭沫若的许多重要著作,是在“文工会”时期写的,另一方面在阳翰笙领导下,专家学者艺术家们在社会上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进步文化活动,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举办各种“名人专题演讲会”、文艺专题讨论会。特别是“时事研讨会”,会上与国民党政客针锋相对、激烈争论,我方每每取胜,引起社会热烈关注。
这些经常举行的集会,每场听众都爆满,阳翰笙邀请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参加,请他们作精彩讲演或者主持讨论,并且通过国民党左派控制的“中苏文化协会”和进步人士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为活动据点,大大发挥了统一战线的战斗力,加强了民主力量的团结,推动了民主运动。艺术家们举办的针砭时弊、激烈抗日的漫画木刻展、诗歌朗诵会和歌曲演唱会更是群众喜闻乐见。
然而,当时最吸引群众的是剧院里的话剧演出。那时重庆有三大话剧团,几乎集中了戏剧电影界的所有人才。阳翰笙和他们许多人都是相知多年的同志或朋友。他奔走在他们之间,一起同风雨、共患难。从创作、演出到生活,无一不给予真诚的关怀。他为他们分解忧愁、出主意想办法,彼此亲密无间、情重如山。
阳翰笙成为许多戏剧电影工作者的知心人,成为戏剧电影界所信任和爱戴的领路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郭沫若的寓所是民主党派、各地进步人士经常出入、自由谈论、互相探讨的场所。周恩来和董必武也经常在这里会客,他们与大家亲切交谈、听取意见、分析形势,通过共同讨论取得共识。
显然,“文工会”不但跳出了“画地为牢”的圈圈,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南方领导的国统区进步文化与民主运动的大本营和司令部。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九千多名指战员牺牲,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为防备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重演,周恩来亲自部署已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及著名进步人士撤离。
阳翰笙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周密、迅速、高效地完成了有组织的撤离任务。最后,周恩来让阳翰笙也回家乡暂避。他回到罗场住了两个月(在这期间他收集了话剧《草莽英雄》的创作素材),局势稍缓后又回到重庆开始新的战斗。
满腔郁愤的阳翰笙思索着在新形势下的斗争方式,他和沈浮等戏剧界人士决意用戏剧作为武器来反击蒋介石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但是当时所有的话剧团体都隶属官方,不可能上演旨在“反击”的话剧。想来想去好像只有一个办法,建立一个民间剧团。
阳翰笙与陈白尘、陈鲤庭、应云卫等人苦心策划、筹备,于1941年10月11日成立了“中华剧艺社”。因考虑政治环境险恶,经济又困难,剧团规模宜小方能灵活机动,所以“中艺”起初只有二十来人。他们都是自愿辞去了固定薪金的工作,却不取报酬、住统舱。三顿都吃稀饭、面条,同甘共苦。演出需要别的演员和人手时,阳翰笙就到各剧团里调兵遣将。
为了冲破蒋介石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周恩来出奇制胜,提出为“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举行纪念活动。他责成阳翰笙负责组建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由各方面人来参加工作。郭沫若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化名人,蒋介石不敢阻挠为他祝寿。周恩来借此,发动各界人士做了一篇民主运动的大文章。
阳翰笙起草一份发党内电报,通知成都、昆明、延安、香港等地党组织同时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动员重庆文化、艺术、新闻各界热烈参加。“文工会”人员全体投入,组织了文章、诗歌、戏剧等多种样的纪念活动。期间,还演出了郭老的话剧《棠棣之花》。延续达半年之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民主进步力量的大检阅。
这是“皖南事变”后,在政治文化领域内反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次巨大胜利。阳翰笙以给郭沫若祝寿的名义,由中华剧艺社上演了他借历史题材反映现实斗争的话剧《天国春秋》。每当剧中人大声疾呼 “大敌当前,我们不应自相残杀!”时,观众席中立刻爆发处雷鸣般的掌声,强烈地表达了对蒋介石政权卑劣行经的抗议和声讨。阳翰笙还一手组织上演了郭沫若赶写的话剧《屈原》,该剧更是在蒋介石头上爆炸的万军雷霆、震撼了山城。
这两个剧所以收到如此巨大的政治影响,还应归功与周恩来的周密谋划。从创作到演出都是他亲自过问,对演出碰到的种种困难,他都一一做出对策性的指示。在《屈原》演出的庆功会上周恩来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缺口。”阳翰笙因劳累过度、生病吐血,未能参加这次庆功会,但他是这两个剧成功演出的具体指挥人和操作者。
“中华剧艺社”促进了进步戏剧运动和民主斗争的紧密结合。“中艺”也因此招致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为了避免损失,也为了将戏剧运动深入基层,周恩来和阳翰笙安排“中艺”以成都为基点,深入到其让中、小县城里去演出达六年之久。演出大小剧目80多种,演出场次在2000场以上,观众约200万人次。“中艺”团队备尝艰辛,成就可歌可泣。
这些伟大成绩的取得,归根结底由于党的领导。“上有胡公(周恩来)这总司令,而始终具体领导着‘中艺’的则是阳翰笙同志。”(陈白尘语),“中华剧艺社”在戏剧运动中起了核心和骨干作用。
后来在重庆,党组织又成立了“中国艺术剧社”。昆明、桂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党领导的民间话剧团。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推动国统区的话剧运动,地下党员们团结广大进步戏剧工作者艰苦奋斗、通力合作。在几年的时间里佳作纷呈、题材多样、演出精湛、群星灿烂,观众趋之若鹜,反响极为强烈。进步戏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为国统区民主斗争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以至后来台湾行政院出版的《中国话剧史》中哀叹:“大陆之沦陷,皆话剧之过也。”
阳翰笙为此,付出了全部精力和心血。于玲在怀念阳翰笙一文中写道:“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是文化界最忙的领导之一。他实际上是周恩来同志的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也是郭沫若最有力的代理人。当时重庆的进步戏剧电影工作人人都叫他阳大哥。有问题时找阳大哥商量,有困难时找阳大哥帮忙。”
1944年,日寇大举进犯。国民党一溃千里,时局危及。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民主斗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文工会”在南方的领导下,经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洋讨论,由郭沫若执笔草拟,郭沫若、阳翰笙等人亲自四出秘密发动签名,于1945年2月22日在《新华日报》和《新蜀报》上发表了有372位文化名人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
时局进言要求强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废除一切压制民主的法令、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废除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等六点政治主张。这一《时局进言》呼出了人民的心声,引起社会上极强烈的反响和热烈拥护,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极大威胁。蒋介石惊恐万状,竟悍然下令解散“文工会”。
在“文工会”告别会上,社会名流们慷慨激昂,纷纷强烈声讨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告别会成了又一次响亮的民主声讨大会。“文工会”成为团结扩大爱国进步人士,贯彻我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的重要活动基地,被人民群众誉为“第二红岩”。
“文工会”被迫解散后,郭沫若应邀访问苏联。阳翰笙的工作岗位转到“中苏文化协会”,代理郭沫若主持研究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他原本是副主席)。阳翰笙和冯乃超为“文工会”的同志们寻找新的工作岗位而奔忙。同时他们继续领导发动、组织文化界人士参加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此后,重庆文化艺术界的民主斗争运动以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和老舍负责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为据点。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在谈判期间,三次接见了阳翰笙等文化、艺术界人士。第一次,到重庆的第三天(8月31日)单独接见了阳翰笙、冯乃超和于玲三人,听取文艺界的汇报。第二次(9月3日下午),又邀请郭沫若、邓初民、周谷城、翦伯赞、阳翰笙、冯乃超、史东山、宋之的等10余人谈话。
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三次,毛泽东在红岩村办事处接见了周恩来领导的秘密政治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的主要领导成员,阳翰笙和王炳南是奉南方局之令参加其中。晤谈达7小时之久,毛泽东赞誉“小民革”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好典型。(“小民革”于1941年夏成立,1949年9月因完成历史使命而解散。)
在抗日战争期间,阳翰笙从事了大量的、千头万绪的组织工作和统战工作。然而,他竟然是抗战期间文艺创作“最丰硕的作家之一”。在这八年里,他写了《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7部大型话剧,还写了《八百壮士》《塞上风云》《青年中国》《日本间谍》4部电影剧本。
阳翰笙首先是一位抗日战士,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跟所有爱国军民、仁人志士一样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站在救国斗争的第一线,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也是一名德艺双馨、著作等身的革命作家,为鼓舞民众抗日斗志、营造抗战文化氛围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正因为他具有高度的革命激情和革命使命感,而且又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底蕴。因此每当人民的命运危亡之际,他的艺术创作又如他内心的呐喊应时代的召唤而诞生。他以难以遏制的革命激情向人们敲起警钟,给人们以激励和启迪。他的作品气度恢弘、壮怀激烈,有高度的思想和感染力,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的大型话剧和电影剧本,无疑是抗日战争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传世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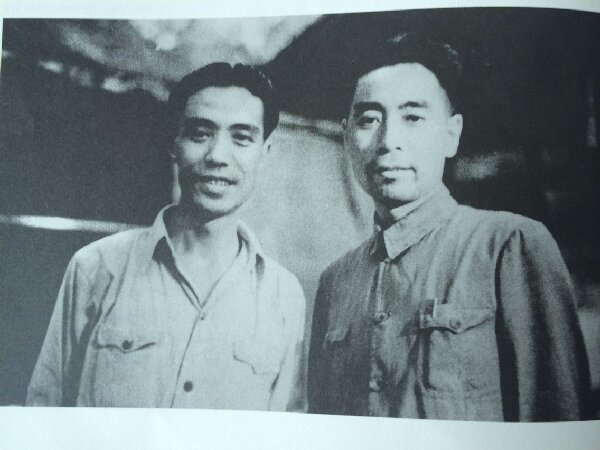
阳翰笙与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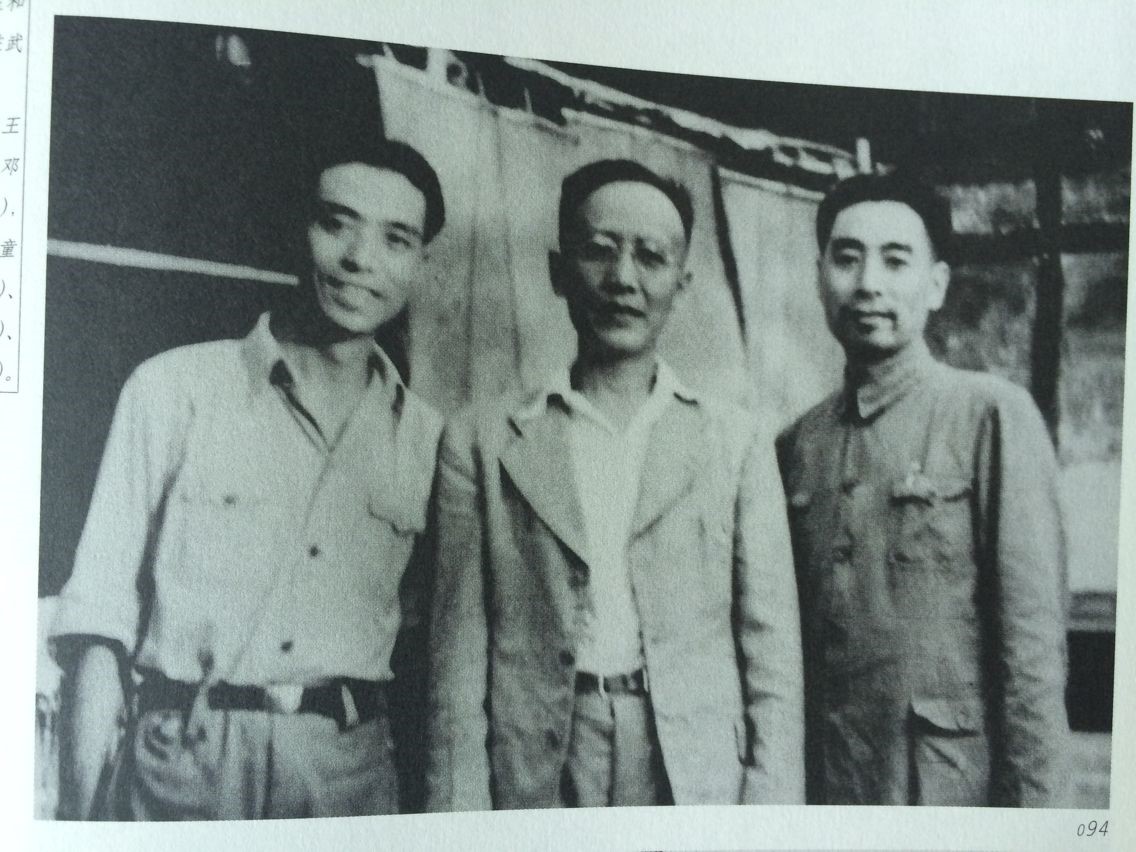
阳翰笙与郭沫若、周恩来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18928111
纠错电话:15116420702(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