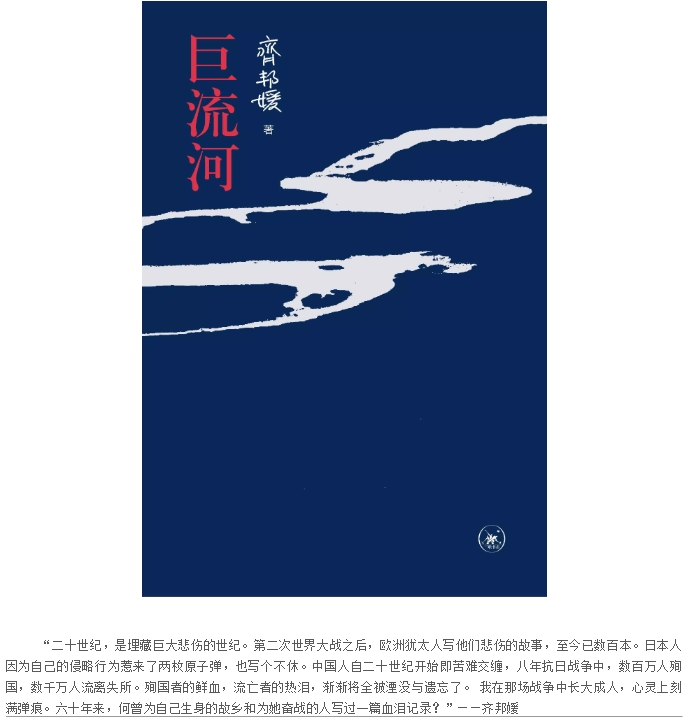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了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
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裳,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我们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个狐穴,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靠着。天晴时,可以看到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看它机翼一斜,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有时,看到我们的驱逐机从反方向迎战,机关枪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有时则看到冒烟的飞机,火球似地向地面坠落。我们心中燃烧着对日本的痛恨,这样的心情,是我生长岁月中切实的体验,很难由心中抹灭。长长的八年,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没有安全感,连蓝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怀?
……
那年重庆被炸得最凶的一次大火后,我们选了一队童子军代表走路进城去共赴国难。走了大半程,只见士兵从未熄的火中抬出无数焦黑尸体由军队运出城,指挥者问带队老师:“这些娃儿(四川话)来做什么?赶快带他们回去!”
我们站在路边拼命哭,一面唱:“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高……”据说回校后,老师被记了大过。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
我至今仍记得有次到歌乐山麓去练旗语的情形。我认真地传递敌情,觉得自己有用得不得了。又因为童子军必须日行一善,每次经沙坪坝镇上回家的路上,总希望能帮助路旁需要救助的人。但那时的沙坪坝已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师生数万人,已是有名的文化镇,轮不到童子军去日行一善,颇令我们感到无用武之地。
初三开学不久,有外国贵宾来访,南开是首站,我和另一个同学被派去大门口站岗。那时我刚升为小队长,童军服(即制服)肩上钉了一卷绳子之类的标示,扎上鲜明的紫白二色南开领巾,手持童军棍,自以为是在做很重要的事。
那天,恰好张大飞由重庆去我家——他已开始驾驶驱逐机与日机作战,经过南开门口,到家后对我母亲说:“我刚才看到邦媛在校门口站岗,她的胳臂和童子军棍一样粗。 ”
我听了不以为意,所有的人都说我太瘦,我反而说胖的人俗气。那时的我,对外表美丑毫无自觉,剪个男发,从不照镜子,甚至对男女有别的种种也很不注意。我的堂姐保冈恰好相反,人长得漂亮,在中山中学读高二,据说是校花。暑假回家,整天照镜子,很看不上我的不修边幅,对我说:“你的童年怎么这么长?”
整个初中时期确实似童年的延长,但从小到处转学的我,从此进入稳定的成长期,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中,得师长之春风化雨,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
那年开学前,妈妈在镇上给我订做了几件浅蓝的和阴丹士林布(洗一辈子也不褪色,到台湾后几乎没看到过)的制服长衫,因为我要上高中了,不能再穿童军服了。有一天早上我穿了一件浅蓝短袖的制服,从家门口小坡走上田埂,走那种长满了草的窄田埂需要灵活的平衡,两旁的稻田在大雨后积满了水,在一低头之际,我看到了稻田水里一个女孩的倒影,那是穿了长衫的我啊!我正伸着双手保持平衡,满脸的快乐与专注。头上的天那么高,那么蓝,变化不已的白云飞驰过去。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在天地之间,照了那么大的镜子。
烽火烧得炽热,炸弹声伴着我们的读书声。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环境成长的孩子比起来,较具忧患意识,懂事得早,心灵却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么艰难的环境,我们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虫咬,白天要跑警报,连有月亮的夜里也不放过。正因如此,剩下的一点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老师说:“不好好做人,就会被淘汰。”就像不好好躲起来就会被炸死那样地谨慎恐惧。每天早上升旗典礼,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南开给我们的这种“敲打的教育”,深深影响我们。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的:“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
……
生命充满反讽,今日思之,确实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时。
我开始谈文论艺是在晴天和月夜逃警报的时候。初中时期思想单纯,常在疏散四郊时讲一讲课本上的难题和同学间的小喜小悲,虽然害怕,有时觉得不上课(尤其早上的数学课)出去跑跑也很有趣。但是,跑掉的课都会在昏昏欲睡的晚自习时补上。
高一那年轰炸得最厉害,伤亡惨重。《时与潮》社在政府号召下,也在山坡下修了一个较坚固的防空洞,里面置一张小书桌和许多木凳,可以容纳二十人左右,装了电灯,备有水与干粮,让编辑部可以一面躲警报一面赶稿子。父母亲也叫我空袭时立刻由小径穿过稻田回去躲警报,学校亦鼓励高中的带初中三五人到安全地方躲避。我常带爸爸好友洪兰友伯伯的女儿洪婵和洪娟回去,解除警报后顺便回家吃一顿饱饭再回学校。防空洞外,死亡的威胁不曾停歇,但在活着的分分秒秒里,听大人们谈论时局、分析时事,对我都是宝贵的启发。那时,轰炸的声音在耳内回响,但防空洞内所读书籍的内容也在心里激荡。回校路上,常是我讲述书中故事的时候,这大概是那个年代舒抚恐惧的唯一方式吧。
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静及幸福岁月的经验,都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的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
回忆六十年前种种暗夜恐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重读抗战历史,即使是最简单、一目数行的《民国大事日志》(一九八九年,台北,《传记文学》),翻到一九四 ○年八月,除国际要闻、前线战报外,记载着:
九日:日机六十三架空袭重庆。
十一日:日机九十架空袭重庆,被我击落五架。
十九日:日机一百九十余架狂炸重庆市区。
二十日:日机一百七十架又狂炸重庆,市区大火,民众损失惨重。
二十三日:日机八十余架空袭重庆。
九月十三日:日机四十四架袭重庆,被我击落六架。九月十八日:东北沦陷九周年,李杜报告,东北义勇军上半年作战共三千二百余次,平均每日对日寇出击二十次。
十月七日:昆明激烈空战。
十二月二十九日:美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示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兵工厂之职务,美国将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
在他著名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今日世上已无处可寻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这是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詹姆斯 •希尔顿(James Hilton,1900—1954)所著《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地名,举世闻名至今。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寇飞机夜袭重庆市,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约三万余人。报道指出,日机投弹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断逃生之路,救难人员在大火中打通两三个出口,隧道内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脸上刻满挣扎痛苦,生还者甚少。这一页页血迹斑斑的记载,可见日本人之狠毒,这样的残忍,促使战时抗日的更大团结。这段历史上不容漏载的国仇,我至今仍感愤怒悲伤。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日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几乎每日一百多架分炸四川各地,有些小城半毁,其目的在摧毁中国人的抗战心防。至十三日,一周之间,日以继夜,无六小时之间隔。重庆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人民断炊,无家可眠,但在这种凌虐下,抗战意志却更为坚强。此日,八十六架又来狂袭,在蒋委员长驻扎的曾家岩三度投弹皆未命中。同月三十日,袭黄山军事会议会场,死伤卫士数人,国民政府大礼堂被炸毁。
整个八月,在与南京、汉口并称为三大火炉的重庆,仲夏烈日如焚,围绕着重庆市民的又是炸弹与救不完的燃烧弹大火,重庆城内没有一条完整的街,市民如活在炼狱,饱尝煎熬。
有一日,日机炸沙坪坝,要摧毁文化中心精神堡垒;我家屋顶被震落一半,邻家农夫被炸死,他的母亲坐在田坎上哭了三天三夜。我与洪婵、洪娟勇敢地回到未塌的饭厅,看到木制的饭盆中白饭尚温,她们竟然吃了一碗才回学校。当天晚上,下起滂沱大雨,我们全家半坐半躺,挤在尚有一半屋顶的屋内。那阵子妈妈又在生病,必须躺在自己床上,全床铺了一块大油布遮雨,爸爸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油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等着天亮……
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精神,也要发出怒吼。
……
一九四一年的寒假在大轰炸中度过。开学后,南开合唱团每天抽一小时勤练由李抱忱老师指挥的“千人大合唱”歌曲。三月十二日先在大礼堂唱,后又加一场在重庆市中心被炸毁的废墟上搭棚架(后为精神堡垒广场),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同声唱爱国歌曲,希望让全城困顿的同胞听到,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让地下的亡魂也听到。我们唱着: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全民抗日的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其作为国歌,来台湾后无人敢再唱。)
那一夜,歌声震撼云霄,所有人热血沸腾,眼泪没有干过,高声唱出积压在内心深处国仇家恨的悲愤。李老师多年后回忆当时情况:“我上台指挥时,看见团员后面是日机轰炸后燃烧倒塌的楼房,听见一千人雄壮的大汉天声。”那股歌声的力量,是太平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