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著名国际法学家大沼保昭梳理了日本民众看待东京审判的两种立场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作者肯定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的同时,认为东京审判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日本国民对此的不作为,使得战争责任论和战后责任论存在种种模糊。
前言
战争体验的思想化
“大东亚战争”是历史上日本民族共同经历的最大历史体验,这是因为“大东亚战争”是日本史上唯一一次全民卷入的总力战。长达四年的战争,几乎涉及国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尽管如此,立足、深化上述体验,并使之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化努力,并未收到丰硕的成果。体验仅仅停留在体验的层面,思想也和体验毫不相干,它只是作为括弧内的“思想”原封不动地被传播着。
作为上述思想化的一次尝试,东京审判与战争责任问题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
“大东亚战争”及最终形成的十五年战争(也称亚洲?太平洋战争或昭和战争),是日本国民倾其全力在中国、在东南亚、在太平洋进行的战争。由于它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战争,所以当战后认定这场战争是不可饶恕的侵略战争——或至少具有侵略战争的一面时,弄清并追究每个国民参与战争的意义也就成为全体国民的任务。自己相信这是一场圣战并加以支持的战争竟然是侵略战争,这到底哪里出了错?自己支持战争该负什么责任?300万同胞的死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并不是说没有这种提问和对这种提问的回答,战后的和平运动以及支撑这一运动的思想,明显是对那场战争的反应。此外,战后日本的经济大国路线也是源于对以前军事大国路线的反省。在此意义上,他们都可以说是立足于国民对战争的评价。但是,我想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对战争的反应仅限于前述的形式,而事实上对战争责任尤其是成为日本侵略牺牲品的其他民族的战争责任,没有成为社会所共有的问题的形式。
当然,东京审判是同盟国进行的“审判”,而非日本国民自己进行的。但无论如何,东京审判是依据难以推翻的法庭证据,对这场日本全体国民卷入的长达十五年的战争,进行公开审判的唯一场所。因为它不是日本自己主导的审判,最低限度地讨论一下如何看待这一审判及其意义就可以了;还有日本国民对东京审判这一盟国的“审判”采取旁观态度,没有创造出一个判定十五年战争的公共场所——上述日本国民的不作为,也应该予以追究。
“战争责任论”的苍白
在以战争责任问题为题材的作品和论述中,并非没有触及上述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些作品和论述在战争责任论体系中,并没有占据中心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战争责任论本身在框定、指导、充实战后日本行动方式方面,并不能称之为战后日本的思想,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尽管高喊‘言论自由’,然而‘言论自由’并没有结出相应的丰硕果实”(粕谷一希:《关于战后史的争论点》,《诸君!》)。粕谷一希先生对此感到忧虑,并讲了下面这段话,从根源上对包括战争责任论在内的战后基本思想进行了批评,涵盖了所有与思想有关的人必须从正面加以回答的问题。
日本应因战败而有所变化。简言之,战后的日本抛弃了明治以后“富国强兵”的路线,走上了一条“富国”之路。但这只是路线不同,日本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以前的日本,当成为“与列强为伍”的军事大国时,已经为悲惨的结局埋下了种子。同样,日本成为“与世界先进国家为伍”的经济大国时,虽然证明了自身具有非凡能力,但同时不也已经开始孕育着新的悲剧的萌芽吗?
如同战前日本纵容军人为所欲为那样,战后的日本也容忍了经济财阀的为所欲为。对此,负有认识世界及其存在方式责任的知识分子,不也证明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知识分子一直在批评日本的现状,但是这些批评不也缺乏有效性吗?战败时,作为总结性自我批评的战后出发点,是不是缺少一些应有的视角?现在需要做的是找出其缺陷,探究战前、战后日本人不变的行动方式,必须改变其性质,或者寻求抑制其性质的方法。
毫无疑问,粕谷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在战争责任论上也是妥当的。到底什么地方有所欠缺呢?在此,通过概括战后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的理解,以及包括有关乙、丙级战犯的著作在内的广义战争责任论,把这一问题搞清楚。另外,还要弄清从这些观点出发本应上升到思想高度而未能达到这一高度的一些遗留问题。
(1)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
关于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在此应确认以下几点。
所谓东京审判,简言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者同盟国在美国占领政策的框架内,在文明的名义下,按照国际法,对战败国日本的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以公审的形式进行的审判、惩罚。具体来讲有以下意义。
首先,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单方面的“胜者裁判”。这一点本身就与公正的审判观念相背离。因为审判的主体应是独立的第三者,不允许一方当事人审判另一方当事人。
不仅如此,在东京审判中,审判一方如同被审判的一方同样具有肮脏的一面。这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向前追溯到长达四个世纪的整个近代史、战争中的行动以及战后行动这三点中得到确认。其一,欧洲列强在全世界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和获取并支配全世界殖民地的历史。其二,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对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苏联破坏《日苏中立条约》。其三,战后以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派兵等为代表的原盟国连续不断地行使武力的历史。
这些可能并不同于日本发动的十五年战争,这也不是要把日本进行的战争正当化。但是,判决一方自己破坏了东京审判的理念,以及其所标榜的“侵略应受到惩罚”命题的道义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上述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东京审判事实上是作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一环而进行的。它带来的结果是审判受占领政策的左右。不起诉天皇、把“偷袭珍珠港”当事者优先确定为被告人以及虎头蛇尾的对甲级战犯责任的追究等就是其具体体现。
第三,东京审判是在“文明审判”的原则下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帝国主义将自己的文化称为普遍的“文明”,而将异文化看做“野蛮”、“未开化”,将对异文化的“教化”、“开化”称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并在世界各地发展殖民地。毋庸置疑,东京审判是建立在上述意识形态路线上的。但是,不可否认,东京审判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军的野蛮行为,表明文明对野蛮的图式具有一定的实体性基础。
第四,在国际联盟、不战条约、联合国、《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中体现出来的战争违法化潮流中,东京审判是以追究国家领导人的刑事责任的形式进行的。原来的国际法并没有领导人责任的观念,它是以国家赔偿责任的形式在事实上要求全体国民承担责任,而免去领导人的责任。与此相比,东京审判具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东京审判仅仅是对一部分旧体制下政治军事领导人的审判与惩罚。即使在政治军事领导方面,也还有对发动和推动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没有被审判。不仅如此,经济、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的领导人也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当然一般国民参与战争的问题也就更没有被提及了。
最后,东京审判是以审判的形式来审判日本发动的这场十五年战争的,被告人是利用整体的国家机构行动的领导人。由于审判的对象是1920年代末到1945年期间的整个战争,很难指望它严格适用英美法系的证据原则。
可是,既然采取审判的方式,作为向法庭提出并留有记录的事实证据,必须经过相应的审查。其结果是,呈现在日本国民面前的,是在当时的时代状况下,通过东京审判弄清的事实,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东京审判以外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尝试所无法比拟的、压倒性的。东京审判作为时代历史上的积极意义,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吧。从今天实证史学的角度,对东京审判的证据以及据此进行事实认定的史料价值进行批评是很容易的,但它并不能否定本文所述意义上的历史价值。而且,虽承认一部分史料缺乏可信性,但总体来看,即使在今天,东京审判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对待东京审判的方法之一——站在旁观者立场上的消极肯定
失之偏颇的全面肯定及全面否定论
问题在于战后日本社会如何面对具有上述性质的东京审判。对此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有人极力批评审判存在的上述各个问题点——天皇的免责、追究主要战犯的责任不彻底、没有审判其他责任者三点,特别是对第一点的视而不见,几乎全面否定审判的意义。另外,还有人认为“大东亚战争”为自卫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这在审判进行之中以及判决决定之后成为辩护团的主流思想以及部分学者的观点,但是仅此而已,并不能引起普通国民的共鸣,至少到1980年代前是这样。
这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东京审判所列举的事实中,不论是“满洲事变”中关东军的阴谋,还是日本在中国、东南亚的残暴行为,在事实上都是无法抵赖的。特别是后一个事实,复员士兵——丈夫、兄弟或者邻居叔叔——在喝醉的时候,偶尔说漏的一句话就符合事实。另外,东京审判全面否定论大部分都带有浓厚的政治复古主义色彩,对统治战后日本以经济为中心的近代化取向的精神构造来说,它总给人一种非常不和谐的感觉。
其次,民众对于上述主张中包含的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复权问题几乎不予认同。对经历过战争的大多数人来说,所谓战争就是战场上如地狱般的日日夜夜,就是失去亲人,就是空袭的恐怖,就是饥饿,就是以战败而告终。迫使国民被动地体验如此悲惨经历的东条及其他领导人受到制裁和惩罚——当然,极少一部分人对他们作为全体国民的替罪羊表示悲哀与同情——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审判的主体及审判基准多少有些疑义,但是他们受到审判本身是正当的。
如同东京审判全面否定论不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一样,东京审判肯定论也没能得到一般国民的共识。在审判持续进行的1947年,横田喜三郎出版了《战争犯罪论》一书。横田先生当时作为东京帝国大学国际法教授,参加了判决书的翻译工作,后曾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务,是日本国际法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他基本上站在与检察方、多数意见判决(东京审判基本采取了英美法的审判制度,判决书依据大多数法官的意见作成,其他法官可以对此持不同意见——译者)相同的立场上,主张对审判的负面置之不理的审判拥护论。他在学界具有很大影响力,却也没有得到学界积极的支持。尤其在一般民众中,他的见解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东条恶魔论与免究一般国民责任
对此,作为应用于东京审判的学术业绩,丸山真男的《军国统治者的精神形态》(1949年)一文与肯定东京审判的一般民众的感觉是相适应的。在这篇论文中,丸山以东京审判中东条、嵨田、东乡等被告人的答辩为靶子,鲜明地描述了这些原领导人是如何“逃避权力”,以及以天皇为顶点的旧体制上的“无责任体系”。他以纽伦堡审判作为比较对象,将同样作为法庭的被告人回答质询的德国纳粹分子戈林,定性为“鲜明地自觉挑战欧洲传统精神的虚无主义者”。对此,他认为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像鳗鱼那样圆滑,像云霞那样暧昧”,表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纸老虎”性质。
毋庸赘言,丸山先生的上述言论不是东京审判拥护论,其意义在于提出了此前国民所不知道的事实,并提供了一个洞察事实的理论框架(其基础是欧美中心主义)。
可是,东京审判不仅否定了战时狂热的日本主义,也几乎全面否定了日本式的存在。它是在全面肯定以“民主”为代表的欧美近代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而且,这种氛围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持续到现在——统治着战后的日本。日本主义不过是对欧美文明的自卑感的反动,但它“仍然”是错误的,欧美“仍然”是了不起的。
在此精神状况下,通过与德国领导人的对比,丸山先生描绘的原日本领导人是只顾逃入权力的保护伞下的小人,他们甚至算不上是大恶人,而是可耻的没出息的东西,从而藐视他们并在价值上贬低他们。作为读过东京、纽伦堡两审判记录的研究者,我对丸山的两审判对比——由此引出的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比——抱有重大疑问。的确日本军国主义者有“向权力逃避”的问题,但这本身并没有错。同样的问题在纳粹的领袖中也不胜枚举。并非只有日本的原领导人“向权力逃避”。
另一方面,丸山描绘的戈林,主动承认自己的“恶”,作为责任主体具有一贯性。在此意义上,给人以颇为“伟大”的印象,难以消除“虽都是坏人,还是欧洲不一样,真了不起”的印象。但实际上在审判的各种场合,戈林不仅企图“逃避权限”,还不时试图向希特勒转嫁责任。与此相比,东条英机为避免追究天皇的责任,把责任揽下来,不更显得“伟大”吗?
从无数历史事实中找出一定的事实并将其作为“历史”呈现,就是史学家的史观。史学家必须对自己的史观负责。丸山真男的史观中明显存在上述意义上的偏颇。怎样评价其偏颇,是伴随我们自身的责任问题。日本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对丸山的肯定性评价,这本身就提出了我们自身的立场问题。丸山的要点在于说明“并非个人堕落的问题……而是体制本身没落的象征”。尽管如此,它还是不免给人一种印象:被告个人一个一个都是胆小鬼。在电影《东京审判》观后感中,有的学生这样写道:“从丸山真男的《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等中,我以为被告都是卑微的、无责任的、战战兢兢的小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以东条英机为首的被告都是昂首挺胸。虽有只顾自己的地方,但该提出的主张都提出来了。”从指出“有只顾自己的地方”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学生的观点还是冷静的,他的上述感想,勾画了丸山论述中的倾向性及存在的问题。
对许许多多的日本人来说,上述原体制领导人的形象正适合他(她)们对东京审判一个方面的理解。如上所述,对日本国民来说,战争只是再也不想遭遇的悲惨体验。早在战争开始时,随着战况的恶化,东条已经成为私下里被埋怨的对象,但是,战败决定了日本国民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关于战败后日本国民对东条的憎恨程度,保坂正康介绍了在广播节目《真相是这样的》中扮演东条的配音演员收到了成捆的恫吓信的故事,并谈到“如果不是在拘留所而是在自己家的话,东条大概会被杀死的”。而东京审判根据事实证据,毫无疑问地认定了使自己陷入悲惨境地的原领导人的责任。在此意义上,大多数国民是接受这一审判的。
同时,东条等人战时连平民的垃圾箱都要检查,惹人反感,战后又自杀失败而招人愤恨。这些东京审判的被告是人类中恶劣的坏人。这对一般国民来说,作为反射性效果,就会自然地免除了自己参与战争的责任。东京审判将一部分原领导层从其他国民的范畴中分离出来进行审判,认为他们是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以战争罪对他们进行了惩罚。正因如此,没有受到审判的一般国民认为,没有受到惩罚就表示没有罪。一般国民就像第三者一样旁观了东京审判。
(3)对待东京审判的方法之二——对同盟国伪善的嘲笑
对“胜者审判”的不信任
如上所述,在战后日本国民中间,存在仅仅因为肯定对领导人的审判、惩罚本身而对东京审判持消极的承认态度。同时,国民中间还隐藏着对东京审判无言的不信任感及难以自拔的感情。
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东京审判的问题点,尤其是与胜者的审判有关,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惑。这个困惑在审判当初就已存在,但是随着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渐渐定格在对审判方的不信任感上。
如前所述,审判者的肮脏之手在三个方面随处可见,第一,欧美列强统治殖民地的近代历史;第二,战时同盟国的行动;第三,战后以美苏为首的原盟国的行动。其中,关于第一,日本自身就是以欧美为榜样成为殖民国家的,但因缺乏近代就等于欧美殖民统治时代的认识,所以对这一条意识不强。关于第二,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几乎是全体国民人人皆知;苏联破坏日苏中立条约,则以站在反共立场的人为中心广为人知。它们与东京审判相联系,从而形成了对审判的不信任感的基础。
在此意义上,后者要远远强于前者。正如前者有代表性的口号——“不再重演过去”一样,并没有追究过去的主体,而是将其定位为面向将来、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与此相反,后者本来就是作为持有反共立场的人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来的。
但是,原同盟国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后行动,让人感到了审判者肮脏的一面。苏联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派兵,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出兵中南美各国,英法出兵苏伊士等一系列事件,使许多日本国民对爱好和平的盟国在文明的幌子下,对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审判的东京审判的原则产生了难以消弭的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感渐渐在日本国民中间扎根。“说得冠冕堂皇,其实你们不是也在干与我们一样的事情吗?反正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东京审判的理念是“文明审判”,正因为它是那样高尚美好的东西,对它的背叛和不信任深深地、坚固地在许多人的心底沉淀下来。
对广田弘毅的同情
日本社会对以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唯一文官广田弘毅为主人公的小说《燃烧的落日》,以及1988年上映后引起轰动的电影《东京审判》的反应,如实地表达了这种不信任感是多么强烈。前者把广田描述为一个抵抗军部的专横统治,但最终未能阻止战争而被处死的悲剧人物。这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引起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共鸣。
在此背景下,电影《东京审判》尽管描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等“大东亚战争”中日本不好的一面以及以投掷原子弹为代表的盟国不好的一面,即两方面都讲到了,但是作为观众的理解,还是比较强烈地倾向于后者。同年,对于曾担任过东京审判法官、活跃在和平研究及和平运动领域的洛林博士的访日,日本社会的反应也是压倒性地集中在他认为广田被判处死刑是不适当的这一点上。洛林博士来日后的报道、采访、“东京审判”国际研讨会上一般听众的提问等,都表现了这一倾向性。
上述反应象征性地显示了许多日本国民对东京审判抱有的复杂心态及郁积。许多日本国民对使自己陷入战败悲惨境地的害人的旧体制领导人怀有怨恨,在此限度之内,承认了对他们进行惩罚的东京审判。然而,另一方面也仍然对盟国的伪善持有不信任感。国民的这种二元评价认为广田不是恶魔,而是人格高尚、值得信赖的人物,将他放在被告席上——而且判处死刑——时,东京审判的意义就凝缩在判处广田的错误这一点上了。
很多日本国民现在一方面依然存在因脱亚入欧信仰而产生的逊于欧美的自卑感。另一方面,也开始具有建立在经济大国意识之上的优越感——这也是前者态度的逆转。对日本国民自己参与“大东亚战争”的事置之不理,增加对东京审判的不信任感,并以这种不信任为媒介,把将十五年战争视做侵略战争的观点贬斥为东京审判史观,把十五年战争总体正当化,这一过程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清晰起来。
战后思想的责任
战后思想的承担者对上述状况负有一半的责任。一方面,为战后日本航向掌舵的政府、自民党、财界、官僚等领导人,并没有陷入“思想”的“观念论”中,而是一味地倾其全力繁荣经济。另一方面,作为言论、理论上“思想”承担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一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对自民党政权,主张“革新”的学者、文学家。他(她)们中的许多人在1980年代之前,都“逃避”了东京审判及战争责任问题。
当然,他(她)们中间也不是没有对东京审判为胜者的审判这一观点表示异议并进行指责的。但是,许多人在战后初期,并不是从东京审判是对镇压国民、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的这种教条的立场出发的,而是出于这样的政治考虑,即明确指出东京审判为胜者审判的一面并加以深入讨论,将会对审判旧体制领导人的东京审判的肯定评价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导致承认战前日本行为正当化。
明确宪法是在占领军的强权压力下制定的事实,对拥护宪法是不利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含糊其辞,对战后保守政权下日本经济的繁荣与社会安定视而不见,而是一味严厉批评日本这里落后,那里水平低。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残酷镇压反体制运动一直保持沉默。与此相同,他们认为对某某情况进行评价,其结果会有利于权力,进而采取视而不见的政治主义思考方式。这一状况导致了战后思想的颓废,并带来了与上述思考的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在今天它不限于东京审判问题,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表现得非常鲜明。而一般民众却不是用上述浅薄的政治主义就能糊弄的,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岂止如此,应该说民众比那些陷入这种政治主义的“思想承担者”要聪明得多。
综上所述,仅从如何对待东京审判这一点来看,战后很多日本国民将自我参与的问题束之高阁,而从第三者的立场出发,承认对原领导人的惩罚,对审判采取“审判者的手也是肮脏的”的犬儒主义。可以说日本的许多国民没有从这个圈子迈出一步。它基本上来自于统治日本社会的脱亚入欧信仰、“外国即欧美诸国”观、“太平洋战争”史观。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和美苏等国的肮脏行径本来就应该分别给予独立的评价。
但是,再重复一下,东京审判是以盟国即他人之手进行的审判,是在占领军的权势下,在不公正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不具有普遍性与道义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加歪曲地对待战争责任问题反而成了找麻烦。那么,为什么日本自己没有开创出对十五年战争进行公共审断的机会,包括这一问题在内的广义的战争责任讨论,究竟要在日本国民参与十五年战争问题上弄清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至今也没弄清就不了了之了,这就是本书下面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选自《东京审判 战争责任 战后责任》一书。作者大沼保昭,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法学家。译者宋志勇,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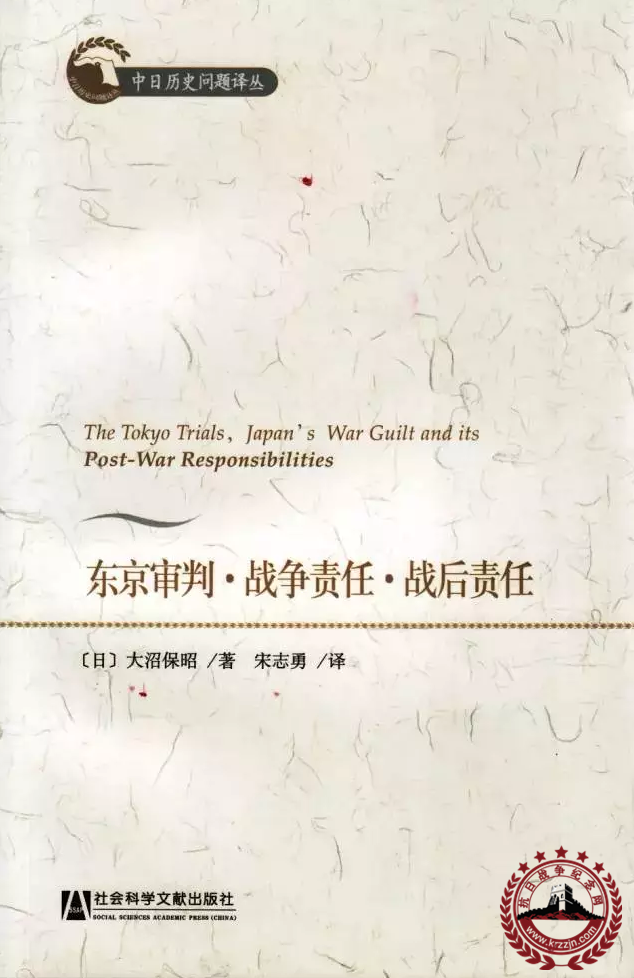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