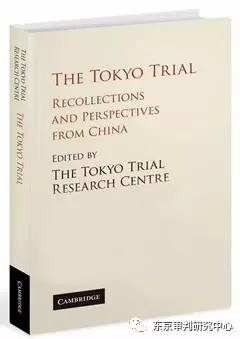
译者按
由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纂的《东京审判文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在2012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引入英文版权,列入“剑桥中国文库”。经过4年多的编辑、删节与翻译,英文版定名为《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The Tokyo Trial:Recollections and Perspectives from China)并于2016年12月正式出版。著名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受该书英文版编辑者之邀撰写了长篇导言。卜先生对中西方相关研究的现状做了率直的评述,与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有相当的不同。不过,不论学术上的观点差异如何,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宽容态度,定能对我们有所裨益。因篇幅限制,《解放日报》刊出时做了大量删节,现将完整译文刊出,以飨读者。

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人,1951年生。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
《作为中国历史的东京审判》
卜正民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玉蕙译(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大将的指挥下开进陷入包围的南京城。国民政府军队无力反击,弃城西去。在此后的七周中,事态逐渐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时间最长和最为惨烈的针对平民与战俘的大屠杀。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时人谓之“南京暴行”(the Rape of Nanjing),本书的作者们则称为“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
日本于1937年夏天发起战争,意在逼迫中国政府让蒋介石下台。首都南京随即成为军事打击的首要目标。日本要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都置于其自身利益之下,但这一要求始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拒绝。日本原打算攻克南京后便终止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然而中国的强烈抵抗迫使日本开始了长期化的军事占领,中国则进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世界也由此被拉入战争状态。直到1945年日本向美军投降,日本在中国的占领才宣告结束。
中国人痛感于日军在战时对平民及战俘施暴与侮辱之深切,始终都在要求一种彻底的纠正。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日两国在东亚的地位发生调转,这种诉求进而愈发强烈。许多中国人至今坚信正义仍未得到伸张,而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中国的历史学者们则通过不断深入挖掘档案文献和屠杀研究主题的内涵作为回应。本书正是这样一种“纠正”主张的成果体现,并且将视角聚焦于战争罪行的司法问题上。
审判德、日领导人的决定源自上世纪40年代初在伦敦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作为这些会议的成果,战后在纽伦堡(1945-1946)和东京(1946-1948)分别进行了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其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也即通常所称的“东京审判”,成为了1993年设立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以前耗时最久的战争犯罪仲裁特别法庭。设立这些军事法庭的目的首先是审判那些将世界导向战争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其次则是通过设立先例来阐明战争的犯罪属性,同时传递出今后发动战争将被置于刑事起诉之下的决心。两个审判在法理和政治上均非白璧无瑕,但它们仍然为此后的战争罪行裁定设立了标准,并且影响和塑造了今天的国际法。

东京审判法庭
九个与日本交战的国家,加上刚刚独立的菲律宾和印度为东京审判提供了法官和工作人员。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渴望中国参与这一事件,并且在众多的申诉案件中尤其关注南京大屠杀的始作俑者是否受到制裁。这一罪行在起诉书里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即第45项诉因:
被告荒木、桥本、畑、平沼、广田、板垣、贺屋、木户、松井、武藤、铃木和梅津在1937年12月12日及之后,通过非法命令,违背诉因2所提及的条约款项,致使和允许日本军队袭击南京城。同时违反国际法屠杀城内居民,非法地杀害和谋杀了数万中国平民和非武装士兵,他们的名字和具体人数至今未明。[1]
法庭最后判定上述所有被告有罪,但却不包括这项诉因。没有一名被告因为诉因45而定罪。这并非因为法庭对南京发生的一切不感兴趣:最终判决书用了8页的篇幅来叙述这场浩劫。[2]法庭也绝不认为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系完全合法。确切地说是因为检方发现要找到能经受住辩方质询并确保定罪的证据太过困难,于是把针对被告们的立证建立在其他方面,也就是引人注目的诉因第55项——该诉因指控除两名被告以外的所有被告“故意并不计后果地无视自己应采取足够措施来确保遵守而不是违反战争法的义务”。六人因此被成功定罪[3],其中松井石根大将和广田弘毅外务大臣两人的定罪原因正是他们在阻止南京大屠杀一事上的明显失职。这也是松井石根唯一的一条有罪诉因,他更是因此上了绞刑台。

被告松井石根正在听候宣判
法庭对诉因45不予以深究的决定使得一些中国人感到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遭到了轻视。一种广泛存在的观点则影响了这种失望情绪,即在伸张正义的方面,纽伦堡法庭做到了东京法庭所没能做到的。这种观点形成的理由是复杂的,不过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和两个法庭的结审情况有关。纽伦堡审判在战争结束后一年之内就做出了判决,东京审判则拖了两年多,直到冷战拉开序幕。到那时,曾经的联盟不再有团结的表象,共同的决定也早已分崩离析。东京判决在日本未能如纽伦堡判决在德国那样被普遍接受,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停滞而中国进入高速发展,这一隐患随即爆发,萦绕于中日关系之间。日本的反应之一就是拒绝为它在半个世纪前的作为承担责任,并且质疑那些出没于日军记录中的暴行叙事,其中就包括了南京大屠杀。这些质疑之声渐渐不再仅停留于南京事件,更将矛头指向东京法庭的判决。他们争辩道:判决书仅仅是为美国在当地实施霸权铺平道路,以及抚慰中国的复仇渴望。[4]
“南京大屠杀”成为公众领域的焦点是在1997年。这一年华裔记者张纯如(Iris Chang)的《南京暴行》(the rape of Nanjing)出版。该书很快就占据了媒体头条并吸引了海外的中国读者——这一群体正越来越感觉与自己的传统割裂,难以将曾经熟知的祖国与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联系起来。同时他们也愤慨于中国范围以外的主流文化是如何忽视了他们的历史。这种重新唤起中国在二战中所受的苦难并向受害者们致敬的渴望冒犯了某些日本人,他们觉得上述感觉只是在心理侧写(Psychological Profile),并质疑战争一代的罪孽是否还得继续由孙子辈来承受。专业的历史学者对该书的评价褒贬不一,他们认为张的感情用事胜过严谨论证,并对她的证据运用提出疑问。不过,在开启公共讨论空间这层意义上,该书的功劳远远超出了此前学者们的工作,而且相关研究也因此而进一步深化,修正了一些我们关于发生在战争首年那场惨祸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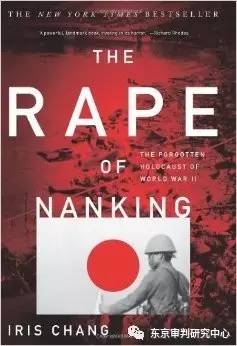
张纯如:《南京暴行》
日本学者鉴于中国人的怒责之深,对进入这一对话领域十分谨慎。而中国学者也因为种种原因同样十分小心。“抵抗”在官方的战争史叙事中占据核心地位,当时的南京城里要是存在任何与“抵抗”相抵牾的事实都会让研究无从下手。一些人还担心在中日经贸关系愈加紧密和重要的时期,这种动摇中日关系的做法在政治上不够明智。上世纪90年代,由中国国家资助了若干个大型的研究项目,但这些研究极少出现有新意的解释。问题的症结在于,它们不是扎根于中国的学术,而是源自中国国家的战后状态。
所谓战后(Postwar),在单纯字面意义上指的是战争结束后的时期,但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对那些捱过战争的国家或是新生政权发生影响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被看作是宣称或享受从极渺茫的概率中成功求生的一种权利。对那些真正经历了战争的人来说,这种权利不仅证明了胜利的正当性,也为那些能使战后的政府和人民重新安定下来的政策背书。而对他们的后辈来说,(战后)则授予他们继续那种荣誉的权利,同时他们也希望战后形成的种种政策在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下去。上世纪40、50年代恰恰是这样一个允许那些生还下来的国家宣称自己可以设立战后秩序或建立新国家的年代——只要他们认为可以巩固自己的政权。[5]法国的查理·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台湾的蒋介石,中国大陆的毛泽东,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哈利·杜鲁门(Harry Truman)和杜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以色列的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方法探索一条战后之路,为他们的政权和政策寻找道德合法性,并平息自身面临的危机。
战后状态不是一份结盟的配方。上世纪40年代末形成的冷战体系不仅仅脱胎于战后,更是通过战后状态所延续,并且让那些最大的战后政权——尤其是美国和苏联——拿着自己的战争记录当作对他国实施霸权主义的权利证明。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人们才有可能开始逐渐分解那些战后被授予合法性的权威。当然,战后状态原本就会随着战争一代或听着战争故事长大的一代相继离世而自然分解。在欧洲,当权者宣称战后状态的消弭始于1968年。当时,出生于战后的第一代人开始怀疑他们从父辈和祖辈那里听来的关于抗争和牺牲的故事只是某个政治神话的片段而已。美国的电影工业倒一直致力于保持“战后”概念的鲜活,直到越南战争的残酷现实将战后体系所依赖的英雄主义一一瓦解。也只有在越战之后,美国的电影人才有可能尝试将二战中的东亚搬上银幕。虽然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在拍摄电影《父辈的旗帜》时仍然遵循了某种修辞惯例,但他小心地避开了美国的战后宣传,选择从日本视角重新拍摄了《硫磺岛家书》。

《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家书》电影海报
不可想象当下有哪位中国导演在面对国家历史上的种种控诉时能像伊斯特伍德那样保持距离,将辩证法用到《父辈的旗帜》与《硫磺岛家书》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非常倚重其战争的记录作为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它必须将日本的占领叙述成一场抵抗战争。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将自己的正当性诉诸于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雄事迹——也就是说双方不得不互相矛盾。随着国民党在2015年败选,这一主张在台湾正变得越来越尴尬和不合逻辑。那个夏天,国民党通过向台湾人宣传和提醒自己在70年前战胜了日本并拥有分享胜利果实的特权,试图以此支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从那些写给公众媒体的可疑评论判断,国民党的竞选宣传并无说服力,尤其是对台湾的年轻人。鉴于台湾在战时曾被日本占领,一些台湾人曾为日本人效力,国民党这种战后身份的遗留达不到其诉求目的也绝不出人意外(竞选宣传包括了由台湾“国史馆”主办的“战争的历史与记忆中的中国史:抗战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战后状态正在台湾迅速消散当中,这也是两岸统一的原本设想越来越缺乏基础的原因之一。
然而,战后权力体系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保持着活力。这可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仍然用它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来支持自己法统的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便不断提醒它的民众(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于1985年建立),中国共产党战胜了日本,它的德行相比欺骗和罪恶的日本更适合做统治者。随着中国的力量在区域日渐扩展,这种做法有利于唤起中国的爱国主义以及保证对党领导的忠诚。由于官方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描述成一场抵抗战争的版本在政权合法性上占据核心位置,对它的极度依赖使得这段历史无法再接受质询。非常多的话题也因此无法开展讨论,例如: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进行了抵抗,一些选择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并非完全因为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国借助了国外的支援与日本对峙,以及中国共产党并非唯一的抵抗力量。[6]相反,人们期待中国历史学者将对日战争描绘成摆脱国外影响的自治、国家的高度团结以及正义必然胜利的历史。[7]这无疑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工作增加了一个显著的负担,他们的责任变成了去证明被认定为真实的事实,而不是探究支撑这些事实真实性的背景。
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这一解释性的语境已经把期待和局限强加给了中国的历史学家。西方学界此前提出的关于审判的种种问题已被证明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得到研究或解决。例如:中华民国在审判中的角色是应该看成美国利益的同伙而被否认,还是看成中国赢得战后世界舞台一席之地的证明而被庆祝?东京法庭上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是应该当成美国人的骗子被解职,还是应该视为国际正义的胜利?审判仅仅起诉28名被告,是否该视为远不及抵偿日本在中国所犯的暴行,还是该考虑当时国际法发展的背景,将这种追究战争领导人罪责的办法视为一种积极的取向?法庭上质询/交叉质询的用途只是英美法中用来防止关键性证据被记录在案的小把戏,还是一种保障充分正义的必要手段?最后,不论是无心还是有意,审判是否未能传递中国的愤怒(尤其是在南京事件上),或者说审判是否实现了正义?
西方的东京审判研究曾一度进展缓慢,但是在过去20年中有了十分重要的发展。据说最早检验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审判中的角色可能始于1999年出版的一部资料集,那是我为了授课编写的。我那时是第一次将法庭的见解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英文文献——这些也是法庭审理的重要依据——相互检证。我将这项工作深入做了两年,在《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文章。[8]这项研究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回应日本否认暴行存在的指控,而是为了减少在中国广泛存在的一种误解,即东京审判未能就南京发生的事件而追究日本领导人。我感觉如若中国人要找到更牢固的论据来回应日本的否认,这个误解需要得到纠正。此后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也相继跟进。在有关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上,中国国内并不情愿关注和评价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承认[9][10]。当然中国学者本身有引用西方研究的责任,反之亦然,但更加充分的对话会对双方更加有利。若不如此,双方的合作空间将大大受限。
有一个例外,即本书的作者之一程兆奇。程早年在上海社科院时便主持了一项关于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中的地位的研究。作为一名日本近代史方向的学者,在2002年出版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论文,包括东京审判是如何审理的话题。其中最杰出的一篇是直接回击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判决书的指责。正如西方否认大屠杀的人士,日本的辩论家们急切地想要把前辈做过的所有错事都移出历史。这种否认做法的危险性在于它离原谅日本战时所作所为只有一步之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默认。程的反击文章成为了他当年稍晚出版的论文集首篇。[11]
在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出版的论文和纪念文章结集中[12],程兆奇的工作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本书的章节,包括程的论文在内,就来自这本结集。在第一部分的七篇学术论文中,程贡献了四篇:2002年的一篇和2007-2010年间的三篇。一篇关于松井石根大将,一篇关于松井的一名辩护证人,还有一篇文章从日本翻拍电影《东京审判》引出广泛的论题,包括解释反人道罪的挑战、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等。第一部分还有中日关系研究学者宋志勇的两篇文章,讨论审判的组织和运作。另一篇合作论文讨论庭审记录中的辩护问题,作者是日本战时占领问题专家张生和日本研究专家翟意安。[13]作者在文章对法庭上关于南京大屠杀一案的宣誓口供和口头辩论进行了仔细阅读,以显示法庭是如何运用于屠杀有关的证词和证据。
本书的第二部分收录了两篇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当事人的见证文章。一篇是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回忆文章。其他东京法庭的法官都已有关于审判的重要回忆著作问世,其中引人瞩目的有反对整个判决的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 Pal)[14],有同时讨论审判长处和不足的荷兰法官勒林(Bert Röling)[15]。相比之下,梅的文章倾向于一篇概要性的回忆而不是法律分析,但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介绍了审判运作的中国视角。在梅的回忆录之前是何勤华的一篇颇有帮助的介绍性文章。何是一名研究中国适用西方法律方面的资深法学家。[16]何教授叙述了梅法官撰写东京审判一书正值文革当中,抄家之时书稿和笔记一并被收走,殊为可惜。梅法官于1973年去世,未能等到可以将这些文稿取回的时日。不过书中四个章节的内容保存了下来,何也得以据此归纳梅法官的观点和角色。梅的文章之前还有一篇另一位东京审判当事人,即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顾问倪征燠的文字。倪征燠为检方关于中国部分的立证工作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包括适应英美法风格的诉讼程序。

梅汝璈法官与韦伯庭长在庭审中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组,前排左起为桂裕(顾问),倪征燠(顾问),向哲濬,吴学义(顾问),郑鲁达(翻译),张培基(翻译)。后排左起为周锡卿(翻译),刘子健(秘书),杨青林(法官秘书),鄂森(顾问)。
本书的标志性贡献在于展现了迄今为止尚未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所知的中国学者的洞见。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界各自为营的情况实在太多,尽管我们的中国同行向中国译介我们的学术工作远远超过我们。随着他们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看法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我们的战后观点(我姑且这样叫)并非今天中国历史唯一的书写方式。进入对话有助于破解战后的局面——某种程度上说它仍然影响着当下的中西方关系。更进一步的话,对话甚至可能有助于破解中日关系僵局,避免现在中日双方相互抱怨的零和博弈。可能这对学术工作来说已经要求太多,但对双方而言,开启对话不啻为一个很好的起点。
[1]John Pritchard and Sonia Zaide,eds.,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New York:Garland,1981),Vol.1,p.54.“Rape of Nanking”曾在起诉书关于桥本欣五郎的个人责任的内容中出现。尽管桥本个人诉因集中在他的部队炮击英国商船“瓢虫号”和击沉美国军舰“帕奈号”,但他还是由于在南京战役中指挥了炮兵部队而受到指控。
[2]Pritchard and Zaide,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vol.20,pp.604-612.诉因45仅仅在判决书中概括所有指控时提到了一次。
[3]应为7人,此系原文有误——译者。
[4]导致出现这种演绎的部分前期工作是由理查德·麦尼尔(Richard Minear)完成的,在《胜者的正义:东京战争罪行审判》(Victor’Justice:The Tokyo War Tria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一书中他表示审判是一场针对日本对外合法自卫的政治攻击。虽然麦尼尔的论述为国际上开启关于审判的争论扮演了关键角色,但他拒绝接受日本应受到战争罪行指控的态度却关闭了与中国同行的交流。
[5]关于“战后”这一概念,参见Tony Judt,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New York:Penguin,2005).关于东亚的战后情况,参见本文作者的”The Shanghai Trials,1946:Conjuring Postwar Justice,”in Postwar Changes and War Memories,ed.Academia Historica,2015),pp.127-155.
[6]这些以及更多的问题见作者著作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Chinese Elites in Wartime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经过很长一段延迟,本书终于得以在2015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分别是《秩序的沦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和《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敵方菁英》(臺北:遠流出版社,2015)
[7]关于中国学者还不曾触及这些问题的观察当然存在一些例外。我想提及潘敏,《通敌》一书的译者,他的早期研究,《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先于我自己的研究。关于通敌问题的新见解可参见李志毓:《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8]Timothy Brook,Documents on the Rape of Nanking(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idem.,“The Tokyo Judgment and the Rape of Nank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3(Aug,2001),pp.673-700.本书重新出版时引用了后者,新版名“Radhabinod Pal and the Rape of Nanking:The Tokyo Judgement and the Guilt of History,”in The Nanjing Atrocity,1937-1938:Complicating the Picture,ed.Bob Tadashi Wakabayashi(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7),pp,149-180.著作和论文后来都收在扩充版的中文译本中,《南京大屠殺英文史料集》(台北:商務印書館,2007),不过未能在大陆出版。
[9]例如叙述审判处理日本暴行的最重要的英文著述,户谷由麻(Yuma Totani)的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The Pursuit of Justice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据我所知该书还未在中国引起关注。
[10]前注所提到的户谷由麻著作已由本文译者翻译完成并出版(户谷由麻著,赵玉蕙译:《东京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法与正义的追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译者注。
[11]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书中的部分内容已被若林正等人的研究所取代,见The Nanjing Atrocity,1937-1938:Complicating the Picture,若林特别在该书的第六章就所谓“百人斩”问题得出结论,认为那是日本媒体的把戏,用来欺骗战时盲信的公众。第六章基本上重复了他早前的文章”The Nanjing 100-Man Killing Contest Debate:War Guilt amid Fabricated Illusions,1971-1975,”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6:2(2000),307-340.
[12]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东京审判文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13]张生与潘敏合作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研究,试图将南京陷落后出现的区域性伪政权进行历史学的表述:《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他在书中的介绍文字是一份希望将通敌历史视作有价值的学术课题的无声呼吁
[14]Radhabinod Pal,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Dissentient Judgment(Calcutta:Sanyal);也可参见他的”International Law,”Indian Law Review 3:1,pp.31-60;(1949)以及Crim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lcutta;University of Calcutta Press,1955)
[15]B.V.A.Röling,“The Tokyo Tri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Indian Law Review 7:1(1953),pp.4-14.也可参见他的一篇介绍文章,见与C.F.Rüter合编的The Tokyo Judgement: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29 April 1946-12 November 1948,1985年勒林去世不久前,他接受安东尼奥·卡塞斯(Antonio Cassese)的采访时给出了非常直率的观点,卡塞斯随后编辑出版了这本《东京审判及其意义:一个“和事佬”的回忆》(The Tokyo Trial and Beyond:Reflections of a Peacemonger,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3)。勒林对东京审判的评价的影响力从采访并编辑其谈话的卡塞斯身上看出一二,他在出版勒林访谈录的当年被任命为首任前南刑事法庭的主席。
[16]何勤华因他在中国法制史方面的研究,三卷本的《中国法学史》而闻名(《中国法学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006)。他同时也进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见《法律文化史论》,北京:新华书店,1998。他关于中国如何适应西方法律问题的观点总结可参见他编纂的会议论文集《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p.537-539.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