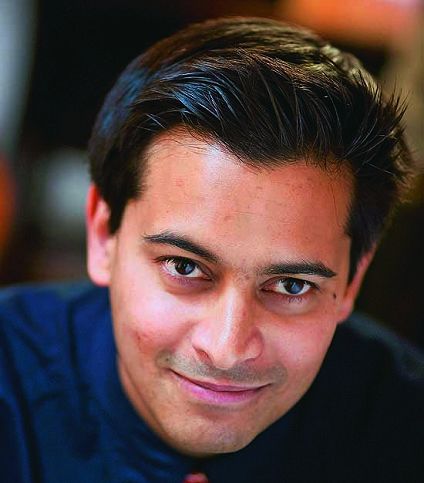拉纳·米特:一个西方人眼里的抗日战争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 2017-02-08 10: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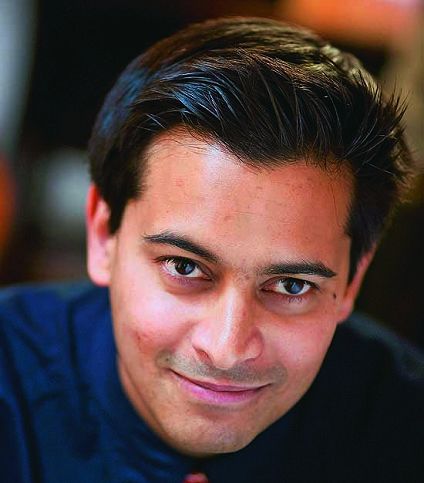 拉纳·米特是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拉纳·米特是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书影
“宛平看上去并不像是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地方。即便在今天,它也只是一个位于北京市西南方向15公里处的小村庄。在1937年,宛平就是一个乡野之地,但它确实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那就是一道用近500头精心雕刻、形态各异的石狮装饰起来的石桥……在中国,人民把它称作卢沟桥。”
对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来说,这座桥意义非凡。这位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选择用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卢沟桥的事件作为他描写中国抗日战争的起源。
在他那部300多页的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美国版名Forgotten Ally: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45,英国版名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一书中,米特认为,随着1937年7月7日事变的升级,卢沟桥的交火开始变得类似于1914年6月的弗朗兹·裴迪南王储被刺杀事件—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是,西方人对这段历史却知之甚少。
在米特看来,“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作用最好应该提醒自己: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
和米特有同样看法的还有一个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7年后的2014年7月7日,在同一个地点,这位强势的领导人出席了纪念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活动,这也是首次有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七七”这一天参与官方纪念。
深谙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米特写道:“研究中日战争是解读中国为何能够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想了解变革中这个国家的自我认同感,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中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不为人知的一面,研究中国的二战史至关重要。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登上世界舞台,承担起区域和全球性的责任。”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米特可能会发现,他的这本书在中国出版的时机似乎恰到好处—一个历史上遭受侮辱的国家,如今正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隆重纪念,来告诉它的邻国以及整个世界,自己已今非昔比。而此时,一位西方学者撰写的强调抗日战争重要意义的著作,恰到好处地应和了中国的叙事日程。
8月22日,拉纳来到中国参加本书的简体中文版首发式。在此之前,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问:
这本书最初是为西方读者写的,后来被翻译成繁体中文在台湾发行,如今又在大陆出版了简体中文版,你对大陆读者有什么特别推荐?
米特:
我希望大陆读者可以理解,他们的战时历史最终在西方被承认了。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亚洲可能都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中国人民付出了1400万个生命以及8000万-1亿难民的代价,他们在战争中遭受惨重苦难。
我也希望中国读者理解,他们的战争经历也是一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中国的很多决策并不是独自做出的,而是在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之间互动的一部分。
问:
这本书在英国的书名叫《中日战争》,在美国和中国则叫《被遗忘的盟友》。在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书名有何特别的考虑吗?
米特:
美国和中国如今有更强劲的关系,有时是积极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因此我想提醒美国读者过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对英国读者来说更不明显一些,因此,在英国我想强调这场战争作为一场全球冲突一部分的重要性。
问:
与西方读者以及台湾读者相比,你有没有期望在大陆读者这里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反馈?
米特:
我认为抗日战争的话题在今天的大陆是敏感的,在台湾或者西方则并非如此。因此我会对中国自身的反应很感兴趣,比如,中国读者会认为这场战争对他们今日的生活和身份至关重要吗?
问:
你在书中聚焦了3个人物的命运: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对中国读者来说,选择毛泽东和蒋介石很好理解,但第3个人为何是汪精卫?
米特:
我想强调汪精卫是想澄清一点,如果日本赢得战争,他可能会统治中国。当然,今天我们会谴责他和日本人合作的决定。但我希望通过诸如他的亲密助手周佛海的日记等这样的材料,来让读者理解为什么汪精卫会这么做。在当时,他的行为看起来符合他的逻辑,即使随后这一决定遭到谴责。
问:
对今日之中国而言,抗日战争留下了哪些遗产?
米特:
我认为中国目标的很多方面都深受这场战争经历的影响:中央集权的政府,对经济变化的渴望,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创造一个空间的渴望,只有这样它才可能有能力保护国家主权。
问:
你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专家,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抗日战争之间有何联系?
米特:
我认为,抗日战争有助于产生把中国建立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想法。但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摧毁性的事件之一却导致了今日中国基于国家之上的强烈的民族主义。
问:
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何时才可以征服或者抛弃所谓的“受害者心态”?历史为什么一直是中国追求富强目标的驱动力?
米特:
我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已经具有了全球影响力并获得尊敬。它已经不需要靠“受害者心态”来让自己的观点为人所知。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更积极的、面向新世纪的国家身份。
问:
由西方主导的日本战后宪法倡导的是和平主义。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尝试修改这一宪法,在集体自卫权方面予以松绑。这一举动是对亚洲安全和稳定的巨大威胁吗?
米特:
这不会对亚洲的安全产生威胁。保持亚洲的安全稳定对美国而言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利益所在,美国不会允许它的盟友让这一地区不稳定。
问:
中国和日本都在西方进行有关战争历史的宣传运动。比如,每当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时,他们总是说,人民应该牢记历史,尊重二战胜利成果等。你认为西方国家是否会支持或者部分支持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米特:
在西方,我认为人们会尊重中国在战时获得的成就,特别是当他们发现更多的史实时,这包括中国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然而,中国和西方都需要意识到,在历史牺牲和今天的政治立场之间并没有简单的联系。时代变了,历史的含义也在变。
问:
中国对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现有的亚洲秩序不满。你认为中美之间爱恨交织的这种关系也根植于抗日战争。那对于今天的中美来说,当它们在亚太互动的时候,可以从历史吸取怎样的教训呢?
米特:
对中美来说,最重要的教训是,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大国们认为,如果一个强国崛起了,另一个必须衰落,这是一种零和状态。我想现在我们意识到这是错误的,在一个地区可以有大小不一的强国共存,它们应该在一个共识基础上互动。中国和美国应该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在亚洲创造一个稳定的体系,中美在这一地区都扮演了角色,这会包含所有各方的牺牲。成熟的大国很清楚,要想保持权力,有时候他们必须放弃一些权力,而且还必须让该地区的其他大国乐于让他们呆在那儿,而不是很焦虑。
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首次出席了纪念卢沟桥事变的活动,在9月3日,中国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这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定后的第一个纪念日,习近平也可能出席有关活动并发表讲话。中国如此重视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是否更多的是现实政治的考量? 米特:
纪念中日战争的这段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战争不应该再发生,人民需要铭记。但在我看来,在亚洲,对于纪念这段历史目前并没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这跟欧洲不同,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以及大多数人民对战争的历史以及战争的意义是有共识的,但在日本,在中国,在韩国,在东南亚,甚至在台湾,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自己国家和地区性的观点。所以我认为,在战争结束69周年的时候,本地区的政治家可以逐渐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和认识。(来源: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