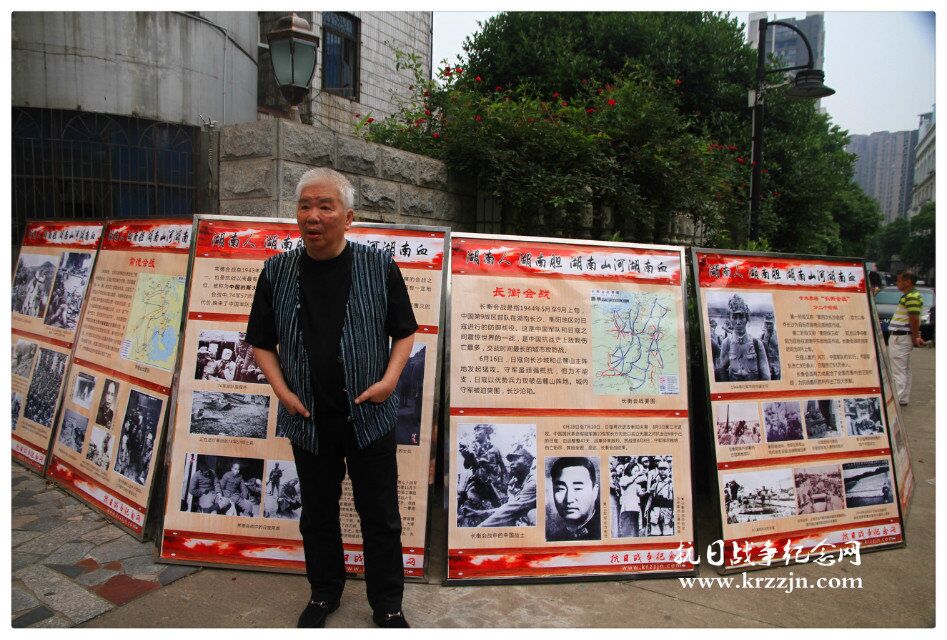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他是娱乐圈的金牌制作人,是李宗盛、费玉清等人出道的幕后推手,也是邓丽君从日本回台后,第一部外景纪录片的制作人。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他是带着执念的抗战纪录片拍摄者。他穷尽后半生,更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素材。他采访了800多名抗战的见证者,其中约有九成已经离世。他手中的大部分素材,已经成为绝响。
作为金牌制作人的他,生活优渥,作为纪录片拍摄者的他,已经一无所有。但他说,“可能我会没有晚年,我还要继续完善这部纪录片。”
抗战胜利已70年,为了这场关乎民族存亡延续的战争,为了这场付出3500万同胞伤亡为代价的战争,我们向陈君天导演致敬,可能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秉持执念的中国人,为留下一部完整、真实的影像资料负责。
晨报记者 陈 承
从世新大学一路北上,就到了八德路。对于陈君天来说,八德路是他历经半个世纪电视制作人生涯中,无法回避的存在——他的制作公司过去和现在的办公地都在八德路; 他效力超过二十年的台视也在八德路; 他曾经拥有的唯一一套房产,还是在八德路上。
延吉街将八德路三段分为东西两个方向。从那里往东步行一分钟,就到了陈君天的卓越传播公司现在的办公地,在马路沿线都是骑楼的格局下,他的制作公司跟一家川菜馆共享一个门牌,外人常常难以找寻。等发现了那条逼仄楼梯,也很可能错走到三楼的住户那里,如果没有过道两边挂有的纪录片海报,制作公司所在的二楼,几乎跟普通住家别无二致。
这是一间南北朝向的屋子,朝北的房间里整齐码放着录像带和编辑机,陈君天的办公室和会客室则朝南,满屋的书架除了摆放与抗战有关的各类书籍外,还有主题是国学、科普、性和人类身体的大部头。
白发苍苍的陈君天穿着《一寸山河一寸血》一片的纪念衫和黑色马甲,指着这些书说,后者归属于他前半生电视制作的经历:当年为了拍摄《认识自己》、《人之初》、《论语》等冷门的节目,他不得不找来这些书恶补,这奠定了他在之后拍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基础。
“八德之狼”弃金牌
台视在陈君天的制作公司正西方向,公交车沿八德路三段坐四站路即到。现在的台视,与台北地标之一的小巨蛋隔街相望,已是繁华地。整五十年前,陈君天坐公交车从“电视公司”站下来的时候,台视周围还都是稻田。
“那时候全台湾只有一家电视台,所以公车站写上‘电视公司’,我们都晓得就是台视。”陈君天回忆说。
其时1966年,陈君天从专事培养军队政工人才的“政治作战学校”艺术系毕业,服完兵役后,考进台视新成立的新闻部,担任新闻美术工作。从250余人中脱颖而出的一大原因,是他小时候在福州生活期间,在驻地部队顶了文官职缺的经历。
“小时候整天挨饿,只有跟着部队才有饭吃,长官看我字写得不错,就让我留在部队刻钢板字。”陈君天回忆,“1949年秋天,我11岁,跟着部队一起开往金门,年底又到了台湾本岛,没想到一去就去了一辈子。”
在部队练就的刻钢板字手艺,让陈君天在台视谋得一份给电视新闻片书写新闻标题的差事。在“写了1万多个新闻片头标题”后,陈君天转型成为综艺节目制作人,期间不仅成为张清芳、林瑞阳、李宗盛、费玉清等等台湾娱乐明星出道的幕后推手,还曾担任邓丽君从日本发展回台后,第一部外景纪录片的制作人。
成为台视综艺节目制作人的二十几年中,陈君天拿遍了包括金钟奖在内的十余个电视大奖。陈君天后来觉得,在那段时间里,冥冥中发生的三件事,日后被证明成为他拍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三大支柱。
首先是他偶然间读到的史学大家吴相湘所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在办公室里,陈君天拿起这本购于1974年、泛黄的书页里注满标记和标签的书说,“它让我第一次直面抗战这个话题,也是我拍抗战纪录片的起点。”
直到拍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第一版,陈君天去美国访问旅居在那里的吴相湘才知道,吴在抗战时期恰是第九战区薛岳部中,管军史档案的参谋,所以此书中准确记录了大量来自吴相湘亲身经历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真人真事。
“当时我作为娱乐节目制作人,觉得书中有太多的故事可以用影像去还原和追记。”陈君天说。
1981年,陈君天开拍以论语为主题的歌舞综艺节目。他觉得,耗时一年所制作的这档略显严肃的栏目,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做综艺节目我点子很多,觉得好玩,但是做完《论语》发现,我也适合做更有深度的片子。我对名利不很计较,也不擅长社会交际,所以一头扎进做冷门节目的非常道里。”
在台视的最后7年,陈君天还负责年终回顾节目《这一年》的制作。这是一档在跨年夜播出的两小时时长的片子,回顾当年的大事件,以及盘点十大最红流行歌曲、电影等等。
陈君天后来调侃说,这档节目本身就是纪录片的框架,那7年里他开始不断累积制作纪录片的经验,似乎正是上天让他静候那通改变他后半生的电话。
台视工作期间,陈君天获封同事杜撰的两个花名:“八德之狼”,指的是他走路虎虎生风;“八德三段勇哥”,形容他即使在冬天,衣服也穿得很少。
陈君天还珍藏着他的台视工作证。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走在八德路上,胸别台视工作证,是件很拉风的事,不仅意味着证件主人有着相对高的社会地位,还能挤进高收入人群。他在台视附近的房产,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买下的。
也是工作证,成为陈君天从台视辞职的导火索之一,“那时候我已经算很资深的电视制作人,无法忍受拿着工作证每天上下班打卡的生活”。还有一大原因是,当时的岛内电视台竞争环境,根本无法为陈君天制作的冷门或主题厚重的纪录片提供支持。
1989年,台视“八德之狼”和“八德三段勇哥”的传说作古,陈君天辞职后开始全力经营自己成立的卓越传播公司。
不变的是,他的公司办公地,仍选址在八德路,只是跨过延吉街,来到了东边。
拍抗战不可行也要行
1994年秋,陈君天的台视老上司刘侃如打来电话,邀他去咖啡馆商谈。陈君天回忆,在刘侃如担任台视总经理的6年里,他从未去过总经理办公室,与刘侃如的关系亦不算密切,接到这通电话感到很突然。
当天下午,刘侃如在咖啡馆开门见山地对陈君天说,“有一件事情,现在看来只有你能做,最近国民党内党政军退休的大人物,希望有专业制作人拍摄一部抗战的纪录片,最好赶在第二年抗战胜利50周年时能播出。”
陈君天猜测,“大人物”们之所以拜托刘侃如来物色人选,与刘的个人经历有极深的关系。刘氏毕业自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留校执教,返台后投身国民党文宣系统,还有外事工作经历。
“他属于国民党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人物,典型的公子哥,在党政军高层有走动,与夫人(宋美龄)的关系也很好,”陈君天回忆,“他在台视做总经理,事情都交给下面的人,当时我们时常开玩笑说,刘侃如在台视喝酒的花费,比公司公车的汽油预算还要多。”
抛出拍片的话题后,刘侃如试探地问陈君天:第一你有没有意愿,第二你觉得可不可行。
“我说,我有百分之一千的意愿,但是这件事不是可行不可行的问题,而是不可行也要行,”陈君天回忆当时他对刘侃如的回答,“环顾岛内电视圈,似乎也没有其他人能做,因为他们一看到这个题目就会吓到,而我在1974年看完的吴相湘那本书,好像冥冥中上天就希望我来做成一件事,这本书在几十年里一直魂牵梦萦着我。”
陈君天还保留着这次会谈后,他写给刘侃如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企划案,其中几处原话是:
“从9·18事变以降,14年间,在日本军阀铁蹄下枉死的中国百姓数以百万计,而今天日本当局却不承认那是一场侵略的战争,只轻描淡写的以‘进出支那’ 四个字带过,至于1937年南京三十万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惨遭屠杀的血淋淋事件,他们更以‘纯属虚构’来掩饰罪恶教育子弟。战后这50年,中国人显然要为从未为自己这场民族存亡绝续的战争,这场付出三千五百万同胞伤亡为代价的战争,留下任何一部客观、通俗、完整、公正的影像纪录而负责。”
刘侃如又为拍片奔走数月,《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最后在1995年春节前后召开,会址选在台北“联合后勤司令部”下属的俱乐部。之所以在此间开会,皆因蒋纬国担任过“联勤总司令”,而他对此片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当天来了二十多位国民党内党政军的高层,没有一位肩上是没有星星的,全场星星加起来大概有上百颗,”陈君天说,“会议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五点,每个人在慷慨激昂地讲述自己在抗战时的故事,那种时空氛围,仿佛完全回到了抗战的时光。”
会议决定纪录片完全授权陈君天的卓越传播公司来拍摄制作,还推选出三位重量级的“监制委员”:蒋纬国、马树礼(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以及夏功权(曾任蒋介石座机驾驶),刘侃如担任执行长。
宋美龄表态只一个“好”字
正当各位热切讨论时,马树礼“泼了冷水”:这件事情我们要做,但有个问题,没有钱怎么做?“会场一下子从嗡嗡嗡的讨论,变得几乎鸦雀无声,没有人能回答马树礼的问题”,陈君天回忆。
好在,夏功权的太太当时在“妇联会”工作,彼时“妇联会”主委正是辜振甫的太太辜严倬云,拍摄资金中的2000万台币,通过夏妻上报给辜严倬云后,由“妇联会”拨款。一个插曲是,宋美龄因长期在“妇联会”担任主委,辜严倬云为拨款一事,还专程飞往美国,获得了宋美龄的首肯。
“据说夫人听到款子要拿来拍抗战纪录片,就说了几声‘好’,也没有提出任何片子中需要忌讳的地方。”陈君天说。
马树礼又四处活动募到了1000万。在开拍前,陈君天和刘侃如专程在蒋纬国在台北的“梅园”宅邸拜访他,陈形容,这是一次拿到“政治免死金牌”的会谈。
“我就跟蒋纬国讲,我们既然是做抗战纪录片,而且看来以后也不会有人再做了,希望片子内容是最真实的,请赋予我全权来拍片。内容事实上的错误我都可以改,但可否免除其它对蒋家和公家的忌讳,”陈君天回忆,“蒋纬国听了马上说,对啊,找你过来做,就是要这样啊,我老子(蒋介石)有什么不对的,照讲。”
陈君天还记得,从“梅园”辞别时,蒋纬国一个劲拍着他肩膀说,“君天啊,好好干”。蒋纬国后来用实际行动支援陈的拍摄,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第一版拍摄素材时,他多次进出陈君天的制作公司摄影棚,谈了很多蒋介石在抗战和晚年的细节。
其中有两个故事被放进了成片里。蒋纬国在片子里说,当年他刚从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受训归来,服役于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三团,去看望父亲时,蒋介石的叫声把他吓了一跳。
“当时战况吃紧,父亲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身高173公分,瘦到只有60公斤左右,因为压力太大,但又没有抒发的管道,只能在洗澡的时候大喊‘天!’、‘妈!’来纾压。”蒋纬国说。
还有一个细节发生在蒋介石逝世前,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蒋纬国在片中回忆,这次家庭聚餐,蒋家的成员都出席了,餐桌上点了蜡烛,佣人在进出餐厅推动房门时,蜡烛被风吹得不住晃动,一如风中残烛。蒋介石这时指着蜡烛说,“你们看你们看,我现在就跟这根蜡烛一样。”
在拍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过程中,像蒋纬国这样全力配合的,并不算多。陈君天说,很多次采访抗战老兵和将领,家人都不愿意支持,担心老人回忆往事会激动,影响身体。好在刘侃如极强的人脉关系帮了他大忙,这时只能由刘侃如出面协调,再介绍陈君天过去拍摄。
空军海军全部打光
也有很可惜的故事。陈君天曾四处找寻先后参加过淞沪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的第十军预备师师长葛先才,后来得知他已经在“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他住在一个单人病房,插着管子,已经不能说话了,我绝不可能、也绝不忍心,让抗战英雄以这样的方式出镜,所以只能放弃。”陈君天回忆。其他将士替葛先才讲述了衡阳保卫战的惨烈:第十师几乎全军覆没,漫山遍野都是阵亡的军人,后续部队赶来,向山顶绝壁的阵地冲锋的时候都不需要搭梯子,因为尸体都已经垒成一座又一座的山。
由于片子计划在1995年9月9日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当晚播出,留给陈君天团队的实际拍摄和制作时间,只有半年左右。而事实上,陈君天又花了两个多月考虑清楚片子制作标准,才真正动身开拍,此时已接近当年初夏。
“在那段时间里,我想清楚一件事,就是只采访亲身参加过抗战的人,学者和专家则几乎略过,”陈君天说,“因为光是历史真相本身,就已经够吓人了。”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是中国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场殊死战役。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道:“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残酷。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
“空军、海军是打光,全军覆没。我们只有100架飞机,全打光了。我们打的是他们的轰炸机,轰炸机的战斗力不强,飞起来的时候要有护航机,他们根本瞧不起你中国人,护航机都没有的时候就起飞。那个时候我们是跟苏联买的飞机,苏联也有飞行员来,我们跟他合作。中苏合作的一个机队在武汉打,照理我们是应该赢的,但是人家掉10架不算掉,我们掉两架就没了。那之后就再没有空军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空军中队长、有大队长,阵亡人平均年龄23岁半。”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们,我们的空军有250架飞机,对方是3000多架。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一样,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泣不成声。
陈君天说,“刚做片子时,我其实很恐慌,生怕很多东西讲得不对,后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优势,就是把能讲清的全部说透,再深的东西,就留给历史学家。”
600美元一分钟的素材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第一版共采访了400余位抗战老兵和将领。但这还不够,片子中还有大量需要引用历史资料画面的地方,陈君天说,为了这些画面,他的团队四处奔走,能花钱解决的都出了大价钱,但还是有很多遗憾。
他听说俄罗斯收藏了众多二战中国战场的资料影像,就只身飞往莫斯科洽购。到了那儿发现,档案馆里确实有不少好东西,但是拷贝费用惊人,对方开出的价码是1秒钟10美元,还不能还价。陈君天还是坚持花费100多万新台币,从莫斯科带回了不少画质极佳且颇具史料价值的资料影像。
当年9月9日晚9点,《一寸山河一寸血》如约在华视播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首集播出时,陈君天团队才制作了前六集作为“存粮”,也就是说,之后将近一年的播出时间里,他们面临每周制作一集的快节奏和巨大压力。第一版做完,公司里18个员工中的9个都辞职了。
彼时,华视设有审片小组,专事审看播出片,是个“不审出点问题,就觉得没有存在感的部门”。但是,当陈君天把片子前六集送去华视后的第三天,审片小组意外地送了很大一份捧花到制作公司,捧花中的卡片上书“此片是电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制作公司的工作表示钦佩”云云。
“我做电视半辈子,之前和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陈君天说。
节目在社会上的反响也相当好——平均收视率破10%,虽远不及当年热门电视剧30%以上的收视率,但仍创下同类型节目的收视纪录。在此片播出的同时,陈君天每周还去蒋纬国所在“中华战略学会”与退役将官研讨片子内容,得到的普遍反映是“片子里很多内容,连打过抗战的老将有些都不清楚”,“可见片子用功之深,大大超过最好的预期”。
除了蒋纬国作为此片推动者积极参加制作和研讨外,蒋家其他人至始至终没有对这部片子作出过任何评论,亦未施加任何干预。陈君天说,所有材料的搜集、梳理和观点的表达,全部是摄制团队自己的取舍和判断,没有任何人来打过招呼。
热潮过后,纪录片“监制委员会”就地解散,没有人提出续拍和完善的建议。让陈君天至今没有放下的,则是刘侃如的“不知所踪”,这位他曾经的老上司、片子的主要推手和联络人,在第一版播完后,从陈君天的视线中完全消失,既没有再与他讨论片子的内容,也没有别的联络,甚至刘侃如在2014年7月去世的消息,也是由其子告知,陈君天才知晓。
“他曾在片子筹备时对我说,他这一生至今只做过一件像样的事,现在他还想做第二件大事,就是把纪录片做出来,”陈君天说,“后来第二件事也做成了,他也许觉得再也没有别的遗憾,没有更多的话要对我讲了。”
“可能我会没有晚年”
自从第一版之后,为了不断更新《一寸山河一寸血》,陈君天变卖了自己唯一的房产、卖掉了汽车、不断缩小制作公司规模和人力。更新片子,成为陈君天这些年来的执念。
“可能我会没有晚年,因为别人的晚年都含饴弄孙,但我还要继续完善这部纪录片。”陈君天说。
在制作《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二十年里,陈君天采访到的抗战见证者已超过800人,其中约有九成已经离世。
“他们的声音已经成为绝响,而让我感到重担在身的是,他们是通过陈君天让大家知道他们在抗战中的故事,这些采访的影像素材,价值不可估量,我绝不可能随随便便地处置。”陈君天说。
《一寸山河一寸血》从1995年开拍第一版至今,已整整过去了二十个年头,五个版本皆在台湾几家知名电视台播出过,引发强烈反响。现在,陈君天感到焦灼的还有另一件事:计划于今年开拍并尝试在大陆电视台播出的第六版,遇到了种种困难,除了资金难题以外,大陆合作伙伴的变故,亦让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感到痛苦而无奈。陈君天说,让心目中接近完美的第六版顺利“登陆”大陆,是他在晚年生命中,最重大的一件事。
其实,陈君天的片子在去年有过一次相对成功的登陆——他参与合作摄制纪念黄埔军校成立九十周年的十集纪录片《黄埔》,在深圳电视台播出。片子中许多珍贵的黄埔学院采访画面,正是出自陈君天这二十年来,为不断更新的《一寸山河一寸血》所积累的素材——庞大的素材库为《黄埔》增添了不少珍贵画面,单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就出现了八位。
《黄埔》的摄制过程相当曲折,数字上的细节就让陈君天颇费思量。比如在黄埔一期,共产党籍学员仅占6%左右,后来几期也只发展到20%,两党学员数量上的对比悬殊,陈君天就此写了解说词:共产党当时规模虽相对较小,但他们送到黄埔来的学生,素质普遍高。
去年11月,陈君天在深圳时,大陆一家电视台下属的版权采购公司老总,曾与他接洽开拍第六版的事宜。
“当时我们两个谈了很久,也几乎达成了合作共识,”陈君天说,“没过多久,大陆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今年10月,第六版有望在大陆播出。但是自那次会谈后,对方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对此,陈君天现在深感焦灼和忐忑,在等待的同时,他仍在资金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多次到大陆为第六版拍摄新的素材。
“没有签约便拿不到费用,干耗的日子令人焦躁不安、夜难成眠。其实我并非不重视钱,毕竟有钱我的片子才做得下去,”在《新闻晨报》采访完成后,陈君天最近给记者新发来的短信说,“许多朋友担心我死掉,他们很干脆地说,你不能死,因为许多东西都累积在你的脑子里,你死了怎么办?也许我死不足惜,可惜的是我未完成的夙愿。”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