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可以零落,但不能遗忘
(代自序)
总理寻访母校,国立中学“开襟”
我自1984年参加工作,一直效力于胜利油田胜建集团。28年来,这个国家一级施工企业在我的人生履历中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2001年3月24日,我作为项目书记受命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自胜利油田基地出发,分乘三辆车远赴四川绵阳,为后续入川承担北出四川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绵(阳)广(元)路项目的大队人马打前站。
一路上,朝行夜宿,十分劳累,而借宿陕西汉中的那个深夜,我却久久不能入眠,因为汉中作为抗战时期著名的“三坝”之一,是父亲当年流亡求学(国立十二中)的地方。
历经6天的长途跋涉,我们一行到达四川绵阳的龙门镇,暂住在一户“农家乐”中。站在“农家乐”的二层露天楼台,美丽的涪江尽收眼底,下游的古城绵阳也依稀可见。抗战时期,另一所以招收山东战区流亡学生为主的国立六中,就在绵阳城里川西北公园(今人民公园)附近。
4月7日晚,我在楼下房东的客厅里看到一条电视新闻:朱镕基总理到湖南花垣县视察工作。花垣是湖南湘西的一座小县城,沈从文先生的名著《边城》就在花垣县的茶峒,而朱镕基总理视察花垣最动情的地方是花垣县民族中学。
在花垣县民族中学,总理摸着院内的石狮开玩笑说:“五十多年一摸啊,谁摸了谁可以当上副总理。”这里曾是国立八中所在地,当时,年仅16岁的朱镕基总理考入国立八中的高二部读书。
朱镕基总理视察当年就读的国立中学,不仅向世人证明了他流亡学生的身份,还意味着党和国家对国立中学这段尘封已久历史的“开襟”。
那是入川后的又一个不眠之夜,为国立中学父辈们“树碑立传”的念头,在我涌动多年的心底油然而生。于是,10多年来的节假日里,整理父亲的讲述,聆听母亲的回忆,联系海内外的长辈及其子女,查找地方史志资料,夜里孤灯勤书,甚至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直到现在,一部30多万字的书稿呈现在我的面前。
真正的历史只能是个人际遇的总和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去后方,说不尽国破家亡。
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
流亡是抗战时期中国极为鲜明的社会符号与标记。日寇的侵华战争使中国遭遇了空前的浩劫,炮火中祖国大地日月无光,铁蹄下华夏生灵涂炭,失去家园、多达上亿的中国人,抛家别子、背井离乡、辗转千里向大后方的流亡,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
如此规模的流亡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整个中国都在移动。军队在移动防御,政府机关、工业厂矿、商业团体和学校在移动,中国的广大民众在移动,这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国立中学的流亡学生。我的父亲就是当年李仙洲将军创建的国立二十二中的一名流亡学生。
那个年代,父辈们最美好的人生年华是在流亡中度过的。72年前(1940年),17岁的父亲从故乡徒步出发,先期到达安徽阜阳,又西迁至陕西安康、汉阴,再度迁移到汉中……1950年,父亲由部队转回家乡工作时已是27岁。
从山东经河南、湖北到陕西数千里的流亡途中,父辈们读到课堂上读不到的“中国社会”这本大书,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获得了很多感性知识。自始至终和流亡学生一道长途跋涉的李广田(山东邹平人,现代文学家、教育家,当时国立六中四分校国文教员)老师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
“我们完全是走在穷山荒水之中,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一词可以代表一切;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
“我们都跑得很结实了,无论是我们的身子或我们的心。我们看了很多,也经验了很多。我们懂得了‘走路’的道理,也懂得了一点生活的道理。”
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所遭遇的人生艰难与痛苦大抵相仿。而就这种痛苦而言,其挖掘意义不是在于自己。所以,许多年来,父亲对那战火连天、社会动荡、流离失所、温饱难求的经历,一直知白守黑,在沉默中守护自身的历史,直到我高中毕业后才断断续续与我谈起。
我读书时的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所以虽然已经高中毕业,但当时还是一个不更事的孩子,无法体察父亲的良苦用心。罪过啊!
过去,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像父亲这样拥有流亡学生身份的人随处可见。而今天,经历了民国社会变革、八年全面抗战和三年内战的父辈们已沉淀为历史的“活化石”,他们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闻听,也成了见证那一段历史的“独家博物馆”。
而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对这些不能泯灭的国家历史,抑或同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因种种原因各自有着不同的版本与说法,其灾难性的后果是导致青年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南辕北辙,甚至怀疑反叛和不屑一顾。
真正的历史只能是个人际遇的总和。自民国以来,中国社会一再分成两半,封建专制的一半,自由民主的一半;日寇侵略的一半,抗战到底的一半……父辈们在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的穿梭中,有着“半边人”独有的通达。
历史上,人们记住的往往是一些波澜壮阔的重大事件,然而构建这些伟大事件的却是一件件鲜活的事和一个个鲜活的人。
作为抗战国立中学学子的后代,我追随父辈们,把他们的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忠实地记录下来,将他们以血泪蒸馏而成的人生体悟与愿望铭刻下来。因为,他们的背后是一代人的命运,是我们祖国的命运。
抗战国立中学
古城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迄今为止,我仅有的两次南京之行其真正目的地同为一个场所,这就是位于中山东路309号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档案馆的历史馆藏分为五个部分,其中馆藏量最为庞大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档案》。在由朱家骅(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教育部部长)题名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之《国立中学概况》中,我查到了以下的史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成立了34所国立中学,在抗战期间累计培育学生10余万人。
当今,一所中学冠以“国立”的名号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的中学多为公立,少数为私立,一般是××市(县)××中学,以××省冠名的也是凤毛麟角。以父亲就读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为例,它的全称是“中华民国第二十二中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抗战国立中学是一个光荣的称呼,它蕴涵着抗日爱国的行动、艰难困苦的锤炼和拼搏奋斗的精神,它还与一串串响彻中国乃至世界的名字联在了一起: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原天津市长聂壁初、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诗人贺敬之、世界著名地理学家许靖华、中国当代杰出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就是抗战国立中学流亡学生的杰出代表。
在战火纷飞、流离失所、忍饥挨饿的岁月中,抗战国立中学挽救了大量战区流亡青年学生,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为国家重建与民族复兴积蓄了骨干力量,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堪称一个奇迹。
一次,空袭警报响了,老百姓四散逃命。
学生问:“还上课吗?”
章用老师镇静地说:“上。”
学生问:“黑板挂在哪?”
老师说:“挂在我的胸前!”
台湾著名作家、英文教授齐邦媛也是当年的流亡学生,这是她在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中对流亡途中学习生活的描述。
章用老师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的儿子,后来病死在西迁路上。
“那时候的孩子,不会为没有生日蛋糕哭泣,只会为国家又沦陷一个地方,为某位叔叔阿姨惨死或受伤而哭泣!”当年随当教师的父母一起流亡、后来因《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红遍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张一弓如是说。
少年的张一弓最先对这个世界产生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弱?小日本为什么撵着我们走?”
看罢这两个细节,你对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历史疑虑就会烟消云散、荡然无存,并肃然起敬。
赢得青年就赢得了未来
这部书稿最初的名字叫《青春温暖着另一个心房》,除了当年的父辈们是清一色流亡学生外,私下里还有吸引青年人眼球的初衷。
2011年11月2日,我应邀参加第二届王鼎钧(父亲国立二十二中同学、世界华文散文大师)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巧遇与王鼎钧来往密切的美国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彼岸》杂志总编辑宣树铮先生。
谈及父辈们流亡求学的经历,宣树铮先生用五个字勉励我:“把它写出来!”
我说:“上年纪的人喜欢看,青年人就不一定喜欢啊。”宣树铮先生回答我还是五个字:“那非写不可!”
“北伐胜利靠黄埔生,抗战最后靠青年军。”这是当年父辈们中流传甚广的一句话。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台湾的同胞也大都记得蒋介石在中国抗战最后关头提出的口号。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大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话更是家喻户晓。
青年是社会的晴雨表,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谁真正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
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不能中断自己先辈的历史,正如出版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台湾尔雅出版社所言:“中国人是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流血成河的年代已经遥远,我们的子孙不该全部忘记,一个没有历史爱恨的民族,他的子民会活得没有方向。”
那个时代的家乡就是浓缩了的中国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故乡是根。上善如水,必有其源,故乡是源。
我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位于山东胶东半岛腹地的大沽河,大沽河的中下游地带便是我的故乡莱西。
“膏腴大沽河,殷实桃花乡。”大沽河滋润延续了被称作“中华第一乐章”的韶乐,是中国古文明的源头和摇篮地带之一。大沽河边有一个叫“韶存庄”的村子,“韶存庄”的最初的含义就是古代的韶乐至今留存在这个村庄。
大沽河最早称姑河。在中国的古文字里,称母亲叫“姑”,母亲在世则称“君姑”,母亲死后则称“先姑”,妻子称丈夫的母亲叫“少姑”。大沽河在命名之初,就赋予了其浓浓的亲情。
“大沽河,无数弯,一弯一个官。”据历史资料统计,仅1840年到1911年的71年间,莱西境内就出了166名秀才、16名举人、10名进士。
抗战时期,日寇在莱西境内窄短的大沽河两岸就设立了八个据点,因而这里也成了家乡人民与日寇殊死拼杀的战场。侵华日寇在胶东半岛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金堂文雄大佐,就是被家乡莱西乡校的军民一枪毙命。
当年,父亲是从大沽河边的家乡出发,踏上了漫漫的流亡求学之路。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家乡工作的父亲,也是在大沽河边的一所学校里认识了小他15岁的母亲。
莱西有名的抗战“拥军小道”在大沽河岸边。当年,路边树杈上挂着的“拥军袋”里,有油灯下母亲搓线、姥娘缝制的军鞋和鞋垫。
母亲的二爹(二叔)是一名抗战游击队员,牺牲时还是一个未婚青年小伙,那是一个寒冬的深夜,地点就在“拥军小道”的对岸。如今,他的石碑立在大沽河边的一个土坡上,立碑人刻的是母亲和她堂弟的名字。
我的三爹(三叔)17岁参军,不到20岁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离校参军的那一天,都没来得及和爷爷奶奶打一声招呼。三爹安息的公墓在大沽河的一条支流的岸边,每次清明回故乡扫墓,公墓的周围都是水雾漫漫、烟气蒙蒙,而我却清晰地记得三爹遗画像中骑着高头骏马、血气方刚、威风凛凛的样子。
王鼎钧先生在看到我记述家乡和亲人们的文字后,禁不住感叹道:“家史即国史,了不得的感动!”
我不是在为我的家乡歌功颂德,也不是在为我的父辈们树碑立传,因为那个时代的家乡就是浓缩了的中国,因为父辈们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他们的经历与回忆是已有文献中所“考证”不到的,却让原本一些不甚真切的历史清澈见底。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历史,或者是宝鉴,或者是包袱,但不应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甲骨文里,“史”字与“事”字结构相似,“史,记事也。”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然而我们记载历史、研究历史却往往随着人的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这其中也不乏来自主观和客观上的歪曲。
毛泽东曾经说过:“读史可以明智,这是先人早就说过的。”
天下之事,熙熙攘攘,分合交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之;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乱之;元一统,明清继之,民国乱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之。
分有分的历史理由,合有合的历史必然,但这都应是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只是在这些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这或许超出了此部书稿所能涵盖的历史容量。
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这就是于国家、于民族、于自己,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因此,国家与民族的悲剧和胜利,抑或父辈们的苦难与喜悦,同样都值得我们年青一代铭记。
正视历史,汲取历史养分,只有这样,历史才会真正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
历史如云,我辈应抬头仰望;历史如雷,我辈需掩耳聆听。
书稿杀青出版之际,我有幸看到一张父辈们的老照片,上方题有《国立二十二中甄试联谊会留影》的字样,落款是“ 三十七。八十四。汉中”,即民国37年(1948年)8月14日于汉中。
这张约有数百人的合影是国立二十二中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照。64年过去了,我们已看不清先辈们当年照片中的位置,但我必须十分清楚今天自己的人生位置。
是为序。谨以此献给我曾经多难的祖国,献给我抗战国立中学可敬的父辈们!
2012年清明于映月堂
后 记
一
《踏不灭的薪火》付梓出版之际,我长达10年“内心愧疚、晨昏颠倒”的生活才恢复了原本的平淡与常规。
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们在追求什么?什么是我们一生一世都应铭记在心的?什么又是我们人生力量的源泉?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对应知的国家与民族抑或父辈们的历史不知所以,反而旁门左道。
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长达14年的抗日血战,无疑是其最为屈辱、最为血腥也最为自豪的一段。而长时期以来,抗战中的“国立中学”和“流亡学生”却一直远离人们的视野,尘封在历史的岁月中。
如今,抗战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之多,可我们中国人跟着这场战争所牵连出来的颠沛流离到今天还没有完结。这不仅是父辈们个人命运的悲伤,也是国家与民族的历史隐痛。
记住这段历史是“知”,明白这段历史缘由才是“识”。作为当年流亡学生的后代,我真正知晓“国立中学”为抗战最后胜利和新中国以及台湾经济文化的历史贡献时,当年“流亡学生”的父辈们大多已离开人世,寥寥无几的健在者也已是耄耋之年。
首先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父亲是当年国立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他的亲身经历与回忆以及提起的事件和人物是我写作的主线。母亲虽不是流亡学生,但也熟知这段历史,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回家聆听母亲的讲述。父亲的回忆和母亲的讲述,有些是在档案馆里查不到的,这是我的“家传珍宝”。
然而对这段复杂性和延续性兼具的历史而言,父亲的回忆和母亲的讲述只是沧海一栗。几经周折,我与北京“会通馆”的周子木女士取得了联系,她寄来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述略》,为我打开了另外一片历史的天空。
这本难得的历史资料,不仅印证了父亲的回忆和母亲的讲述,还详细记载了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流亡经历和历史变迁,并收录了数千名教师和流亡学生的名字。在《学生名录》的第308页,我找到了父亲的名字。
走吧,踏着父辈们的足迹。十年间,我走访了父辈们当年流亡求学途径的许多县城,每到一地,档案馆和史志部门是我必去的地方。参考的回忆资料撰写者绝大数已不在人世,“人将死,其言善”,我信。因此,《踏不灭的薪火》中提及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有案可查、经得起历史考究,我称其为一部非虚构历史文学作品。
真正的作品只能是作者个人思想的沉淀,但对书稿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我极少有主观评判的文字,因为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牢牢记住也秉承了父亲的一句话:“不能因为谁是执政党就说谁昏庸无耻、反动透顶到家了,也不能站在政党的立场上来谴责民族过去的历史”
早期创作时,得到了父亲国立二十二中的同学、今客居美国的当代著名华文大师王鼎钧的勉励。那时,鼎公(人们对王鼎钧的尊称)刚做了眼科手术,看了部分章节后大发感慨:“家史即国史,了不得的感动!”
书稿草就后,因山东苍山县原史志办主任穆振昂先生介绍,我受邀参加了2011年11月在山东苍山举行的第二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听取我的大会发言后,美国旧金山“华文文艺界协会”名誉会长刘荒田先生和美国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宣树铮先生,以及海南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50——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关联研究》的毕光明先生,当即鼓励我将书稿结集成书。
这年年底,我出差烟台,巧遇胜利油田文学期刊《太阳河》副总编朱卫良先生,可谓心有灵犀、一见如故。卫良兄不仅亲笔斧正百余处,并留下了“新古船”的评语,最后的书名《踏不灭的薪火》也是他“一锤定音”。
我的同事张金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女士倘在哺乳期,竟费时数月对书稿中的错别字给予了修正。我的挚友胜利油田青年书法家任维淸先生,在出版社未定稿之前就“四处宣传、广造舆论”,乐此不疲。
应该感谢的还有一代爱国抗日音乐家、原国立六中四分校音乐教员瞿亚先的长子瞿雷先生,他为书稿提供了一些详细资料和数张珍贵的照片。另,夏威夷女士也将其父亲夏继昌先生当年拍摄的老照片无私提供给我。
尤其是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韩怡宁女士,作为一名专业编辑,她看完书稿后先是将其推荐到一家名气颇大的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辛劳颇多,特表谢忱!
不能忘记的还有我中学的语文老师孙愿先、地理老师李永芝和历史女老师綦进香,没有他们教授我扎实的中文、地理、历史知识,这本书稿恐怕难登大雅之堂。
二
第一次读台湾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是2010年的初冬。大陆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书(首版于2009年台湾天下文化公司),获得了2010年亚洲出版奖最佳著作类首奖。
那时,《踏不灭的薪火》倘在紧张的写作中。我只浏览了个大概其,就不敢再继续读下去。因为,齐邦媛(1924年出生)与父亲(1923年出生)是同一个年代的流亡学生,她的《巨流河》和我当时的书名《大沽河》都以各自故乡的母亲河命名(巨流河即今辽宁的辽河,大沽河是山东胶东半岛的第一大河),而且两部书稿第一章的标题均是《歌声中的故乡》(正式出版前,我的书稿第一篇改为《水集之地的故乡》)。
齐邦媛出身名家,其父齐世英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毕业,回国后官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并创办了著名的中山中学,而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晴耕雨读”的农家子弟,但他们经历的流亡时代背景是一样的。我害怕深陷齐邦媛的《巨流河》其中,导致文字上有雷同,于是将《巨流河》放在一边,专心于自己的写作。
《踏不灭的薪火》杀青后,我曾投稿三联书店,不曾料到三联书店婉然谢绝的原因之一就是“此前已出版过齐邦媛的《巨流河》”。而真正令我遗憾的不是这些。因为,当年国立山东数千名流亡学生我能联系到的仅有十几位,即便是这十几位,我也无法一一前往拜访。他们是:
张师云(现名张纪元),祖籍山东山东文登,妻子(上海人)也是流亡学生,就读于当时的中央大学(重庆)。1945年春,他和陈金典、于鸿运、李汝信三个同学写的《讨郑檄文》,为国立二十二中学潮运动(当时四大学潮运动之一)做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新中国成立后,张师云和妻子一直在山东平度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现居上海。
孟秀华(现名孟辅),山东济南市长清县人,国立二十二中西迁途中“韩庄惨案”时曾被日寇抓住捆绑押走,后被校方营救出来。毕业后考上西北农学院(现陕西农大),1951年应招到黑龙江牡丹江的东北空军第7航校学习,成为共和国第一批(全国有55名)女飞行员,试飞三个月后到东北空军政治部任职,后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到吉林工业大学做行政工作直到离休。孟阿姨现居吉林长春市,听力不好,有一女儿在身边。老人一再问我:“你什么时候来长春?”
蒋志芳,祖籍山东单县,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市财政局和国家审计署任职,现居北京,三个孩子,两个在美国和法国,一个在北京,通话十几分钟,声音响亮,性格开朗,耳聪脑明。蒋阿姨一再叮嘱我;“你要快点来北京,我们都八十多了。”
现居北京的佟三和她的爱人马俊同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是封面设计的专家。曲季涛和她的爱人李信也是当年山东的流亡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同在新华社工作,现居住北京,一个失音、一个失明……
他们的经历与故事也不知还要雪藏多少年!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
至此搁笔,算作后记。
2012年11月28日于映月堂
历史可以零落,但不能遗忘
——《踏不灭的薪火》的作者王安民访谈录
(作者简介:王安民,山东青岛莱西人,1984年12月参加工作,1991年6月毕业于山东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先后从事宣传、青年、项目管理和工会工作,现任胜利油田胜建集团工会副主席。曾在报刊发表《难忘的岁月》、《铺在天国上的路》、《大风起兮云飞扬》、《雄关漫道霜晨月》、《来吧,偷走我吧》、《梦回大川九》等纪实文学作品,参与编辑了胜利油田孤东油田会战纪实文集《在这块热土上》,有作品收入《民族的脊梁》和《世纪大道》。)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王老师,首先恭喜大作出版问世。与刚出版的《踏不灭的薪火》一样,广大读者对您本人也是很陌生的。请向《胜利电视周刊》的读者介绍下您自己好吗?
王安民:我自1984年12月参加工作,一直效力于胜利油田胜建集团。近30年来,这个国家一级施工企业在我的人生履历中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回顾过往,仅有两件可圈点的事:
首先是我和我的团队修筑的川北高原上的川九路荣获了詹天佑大奖,再者是我历经10年写就并出版了记录抗战时期父辈们流亡生活的长篇纪实《踏不灭的薪火》。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文学创作需要灵感。您是何时萌生《踏不灭的薪火》写作念头的?
王安民:真正的文学创作灵感只能来自于人生的历练与感悟。2001年3月24日,我受命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远赴四川绵阳工作。自油田出发,一路循着黄河两岸西进,翻越秦岭就是汉中盆地。作为抗战时期著名的“三坝”之一(另是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汉中是父亲当年流亡求学(国立二十二中)的最后一站。抗战时期,另一所以招收山东战区流亡学生为主的国立六中旧址也在我们此行的目的地绵阳。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给了我强烈的心理刺激。人应读千卷书,更需行万里路,道理就在于此。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这是时空上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王安民:如其说是时空上的巧合,倒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2001年4月7日晚,我在房东家看到一条电视新闻:朱镕基总理到湖南花垣民族中学视察工作。这里曾是国立八中所在地,当时,年仅16岁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的高二部读书。朱镕基总理视察当年就读的“国立中学”,不仅向世人证明了他“流亡学生”的身份,还意味着党和国家对“国立中学”这段尘封已久历史的“开襟”。这促使我下定了写这本书的决心。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当今,对很多读者来讲,“流亡学生”和“国立中学”还是相当陌生的名词。
王安民:流亡是抗战时期中国极为鲜明的社会符号与标记。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流亡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流亡学生”。在存亡断续的关头,教育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为了挽救民族教育,陈立夫任部长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从根救起”, 从1938年到1942年在抗战的大后方先后成立了34所国立中学。一所中学冠以“国立”的名号,这在当今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现在的中学多为公立,少数为私立,一般是××市(县)××中学,以××省冠名的也是凤毛麟角。以父亲就读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为例,它的全称是“中华民国第二十二中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还原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王安民:真正的历史只能是个人际遇的总和。今天,经历了民国社会变革、八年全面抗战和三年内战的父辈们已沉淀为历史的“活化石”,他们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闻听,也成了见证那一段历史的“独家博物馆”。历史上,人们记住的往往是一些波澜壮阔的重大事件,然而构建这些重大事件的却是一件件鲜活的事和一个个鲜活的人。作为抗战国立中学学子的后代,我追随父辈们,把他们的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忠实地记录下来,将他们以血泪蒸馏而成的人生体悟与愿望铭刻下来——贫穷落后就会挨打,中国人内斗外强就会有机可钻。于国家、于民族、于自己,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正视历史,汲取历史养分,只有这样,历史才会真正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听说《踏不灭的薪火》是三易其名?
王安民:书稿最初的名字叫《青春温暖着另一个心房》,除了当年的父辈们是清一色流亡学生外,私下里还有吸引青年人眼球的想法。青年是社会的晴雨表,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谁真正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而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对一些不能泯灭的国家历史,抑或同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因种种原因各自有着不同的版本与说法,其灾难性的后果是导致青年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南辕北辙,甚至怀疑反叛和不屑一顾。之所以改名,是因为我不能去选择读者,而是读者选择我,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青年人能读读这本书。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现在社会上在热议“中国梦”,“国立中学”和“流亡学生”与“中国梦”有怎样的关联?
王安民:“中国梦”不是凭空掉下来的,鸦片战争后叫“振兴中华”,抗战时期喊“收复失地”,抗战胜利后称“民族复兴”。我写《踏不灭的薪火》就是要告知人们,当年“国立中学”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流亡学生”的父辈们为打击日寇与民族复兴发挥了骨干力量。有一个许多人不了解的史实,就是抗战后期中国主战场的主力部队是流亡学生组成的“青年军远征军”。10.5万“青年远征军”是清一色的知识青年,最低学历是初中生,其中专科以上仅有2500人,绝大数是“国立中学”的青年学生。还有,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诗人贺敬之、中国当代杰出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也是当年的流亡学生,他们为民族复兴的贡献彪炳史册。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踏不灭的薪火》先后历经10年,写作的困难可想而知,谈一谈这方面的感触。
王安民:《踏不灭的薪火》纯文字写作用了3年,而收集资料却用了7年,因为我不能去凭空想象父辈们的历史。我的父亲是当年国立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他的亲身经历与回忆以及提起的事件和人物是我写作的主线。几经周折,我得到了大陆市面上仅存1本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述略》,这本及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为我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天空。同时,我开通了博客,一些流亡学生和他们的子女为我提供许多比书籍档案更为鲜活的历史细节。所以,我称《踏不灭的薪火》是一部非虚构历史文学作品,里面提及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有案可查、经得起历史考究。作为“流亡学生”的后代,我必须忠实于父辈们的历史。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踏不灭的薪火》记录了许多历史人物,最让你感动的有那几位?
王安民:父辈们的老师们。国难当头,军人的使命是浴血疆场,而保全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老师们的使命并不比上战场轻松。有一位叫张荫轩的化学老师,在讲水分子一节时说:“当你逃离沦陷区奔来大后方时,你的母亲流下的那一滴眼泪,就是水的分子组成的。与泪水同时存在的还有感情。水分子是物质,感情是精神,泪水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体。”英语老师吴惠波老师,每堂课她都要先领着学生大声朗读:“We are Chinese, we love China, long live China!”(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中国,中国万岁!)音乐老师瞿亚先说,日寇占领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只剩下唯一的喉咙了,西迁路上,他带领自己任团长的“狂飙剧团”,演出剧目44个,正式演出70多场,观众达8万余人,街头宣传和教唱抗战歌曲不计其数,累计募捐数万元,除维持基本生活,悉数转送给抗战前线将士……大学非大楼也,应有大师也。现在的政府部门、企业和学校缺少的不是“大楼”,而是缺少像父辈们的老师那样的“大师”。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粗略地通读了一遍《踏不灭的薪火》,发现书中不乏“小日本”、“日本狗子”等字眼。时下,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国人的仇日情绪剧增,谈谈你的看法?
王安民: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双目失明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历尽艰险,六次东渡,带去了佛学、中医、建筑、绘画,日本开始“衣冠唐制度,文物汉宫仪”。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其《日本历史》中写道:“日本社会就是这样: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贪婪地吸收了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进入了文明阶段。”然而蒙受中华文明恩泽的日本却发动了极具凶残血腥的侵华战争,把伤痛和愤怒长久地撒向了中国人民的心底。想起曾为国立中学捐款5000大洋的宋哲元将军,他生前经常下部队与士兵进行如下的谈话。宋哲元问:“我们最怕的是谁?”士兵回答:“老百姓!”宋哲元又问:“我们最不怕的人是谁?”士兵回答:“日本人!” 9月18日是“国耻日”,宋哲元规定每年的这一天,全军将士只吃一顿饭,每人一律一个馒头,上面还清楚地印着“勿忘国耻”四个黑色大字。诚然,我们应记住的是历史而不是仇恨,但一个没有历史爱恨的民族,他的子民会活得没有方向。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踏不灭的薪火》的历史涵盖面广,里面既有老牌的国民党员,也有老资格的中共党员,似乎超越了国共两党与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
王安民: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之;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乱之;元一统,明清继之,民国乱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之。分有分的历史理由,合有合的历史必然,但这都应是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只是在这些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所以说,不能站在政党的立场上来谴责国家与民族过去的历史。当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晚年曾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历史如云,我们应抬头仰望;历史如雷,我们需掩耳聆听。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踏不灭的薪火》刚出版不久,社会上有怎样的评价?
王安民:《踏不灭的薪火》刚完成初稿时,远在美国的王鼎钧先生看到后,为我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家”历即国史,了不得的感动!王鼎钧是国立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当代世界著名华文大师。有这样的评价,我不再有任何奢望。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谈一个细节,《踏不灭的薪火》出版后的第一本,您送给了谁?
王安民: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虽不是流亡学生,但也熟知这段历史,我从一线回到机关工作后的那几年,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聆听母亲的讲述。我没有录音,也不做笔记,只是静静地聆听,母亲的话我记在了心底。书中有许多文字都是对母亲讲述“原生态”般地记录。春节放假前,我拿到了《踏不灭的薪火》样书,大年三十上午陪同领导下基层慰问一线职工回到家后,我将《踏不灭的薪火》作为新春礼物送给了母亲,母亲一看到书的封面就落泪了……爱祖国、爱民族,首先要爱我们的母亲。
《胜利电视周刊》记者:谢谢您接收《胜利电视周刊》的采访。
王安民:也谢谢记者先生。祝《胜利电视周刊》越办越好。
《踏不灭的薪火》:王安民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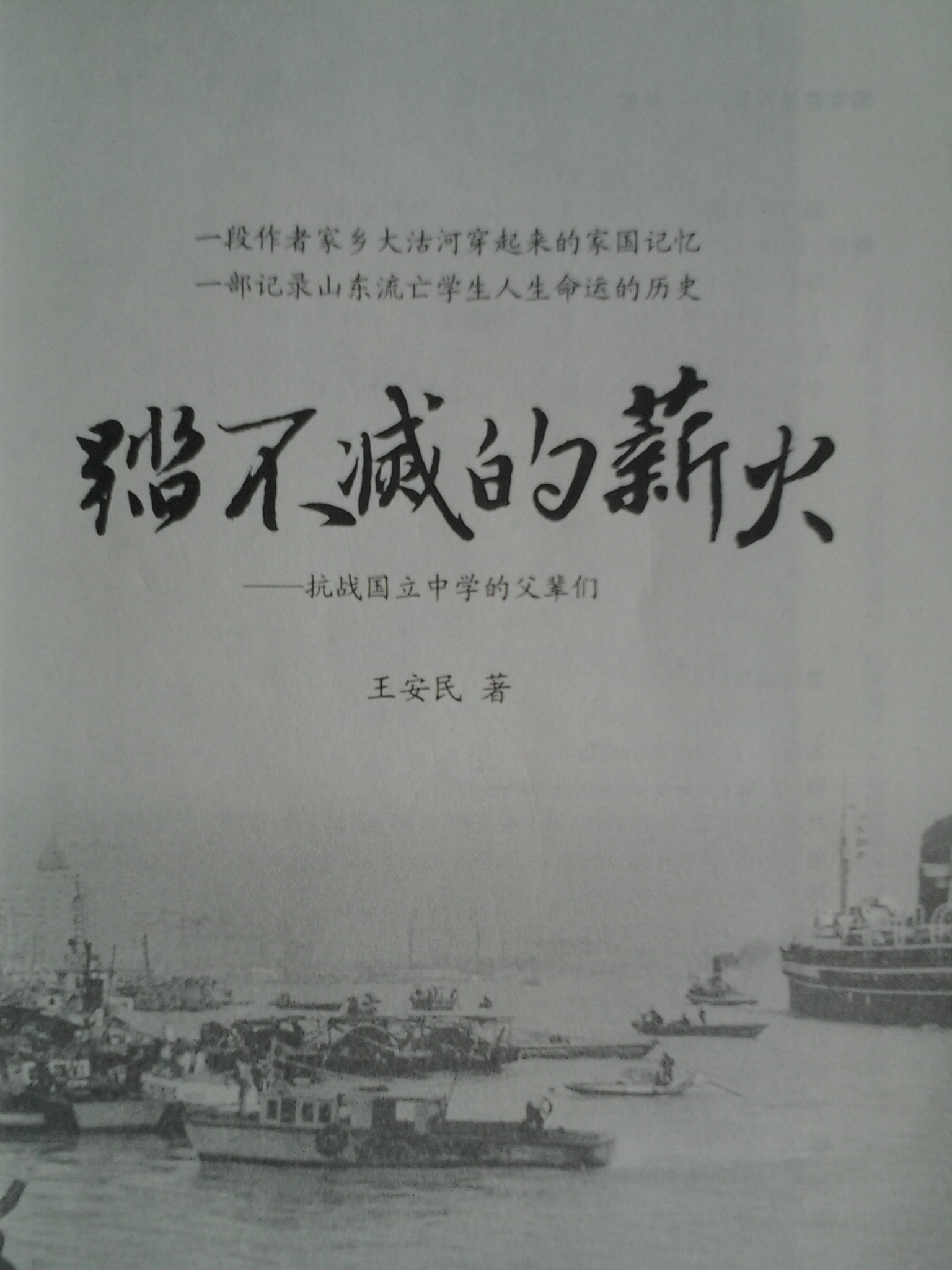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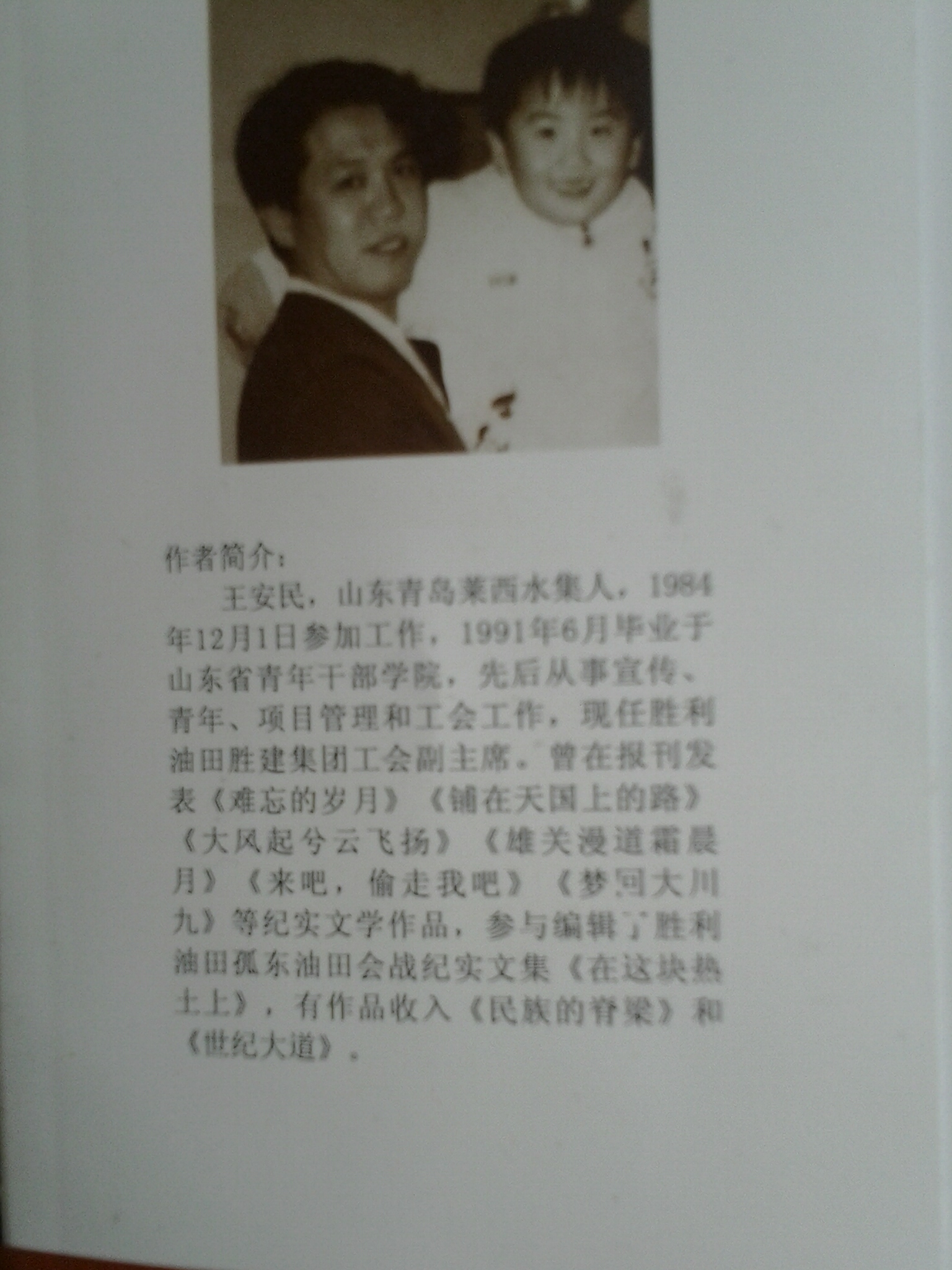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